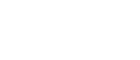中图分类号:J18-2;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041-09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hemes, styles, constituents of donor figures, and artistic functions of Western Xia dynasty Buddhist cave murals from Dunhuang and Guazhou, and considers that the cave art of Dunhuang and Guazhou exhibit differing characteristics due to clear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situation respective to each region. In turbulent Dunhuang, although a passion for creating Buddhist art had been inherited as a result of historical inertia, activities were confined to rebuilding or painting existing caves; whereas in relatively stable and powerful Guazhou, a new group of caves were constructed that reflect in a concentrated form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culture and art produced by the Western Xia.
Keywords: repainted wall paintings; construction of new caves; region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Xia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西夏?y治时期(1036―1227),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古称沙州)与瓜州(原安西县)的历史状况有明显的差别。瓜州在西夏建国初期就成为夏国十二监军司之一,是西夏政权西部边境的统治中心,也是与回鹘人争夺沙州等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政治、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临近的敦煌则相反,长期处于不同地方势力争斗影响之下,局势动荡。不同的历史状况,使这两个相邻地区的佛教艺术呈现出很不一样的特征。
一 瓜、沙西夏石窟营建的历史背景
瓜州与敦煌是紧挨着的两个行政区,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敦煌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居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各方面的影响力,也比瓜州大得多。但在西夏统治河西地区的历史时期,情况与过去明显的不同:敦煌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政局不稳,经济发展滞后;而同时期的瓜州,则成为了西夏政权最西端的统治中心,设立了直属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监军司,是西夏国前期的十二个监军司之一,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程度都比敦煌高,佛教石窟的营造数量和质量,也相对更多更高。
西夏军队于公元1036年攻占沙州,开始统治整个河西地区,敦煌成为了西夏最西端的领地。由于沙州回鹘人的顽强抵抗和连续不断地袭扰,西夏统治下的沙州战乱不止,统治权也可能时有易手,以至于部分学者相信,西夏对敦煌的稳定统治应从1070年开始{1}。也有人认为西夏二次占领并长期统治沙州,始于公元1067年[1]。有人甚至认为,公元1146年辽国覆灭之后,西夏才完成对敦煌的完全统治[2]。也有学者坚持认为,西夏从公元1036年起就一直统治瓜沙地区[3]。以上诸家论断,归纳分析起来,有两个共同点:一、学者们大都同意自1036年起,直到1146年为止的110年间,沙州是回鹘人与西夏人争斗的战场,政治形势并不稳定,经济也未得到正常的发展;二、诸位专家的研究,大多把沙州和瓜州合并在一起讨论,很少有人把瓜州和沙州这两个行政单元的历史做分别的研讨。
我们通过对现有原始资料的梳理和对已有学术成果的分析,认为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有两个局限:
第一,把沙州和瓜州混同在一起讨论。这样做,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沙州和瓜州在西夏时期的历史是完全一致的。把瓜、沙二州的历史放在一起讨论,对西夏统治之前的归义军时期而论是合理的。然而,西夏攻占河西地区后,在瓜州设监军司(瓜州西平军司),驻扎常备军队,对瓜州实施了较为稳定有效的统治,因此,瓜州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后来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而同时期的沙州则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社会状况很不稳定,经济民生难以发展。
自1036年西夏占领沙州之后,“沙州回鹘”仍然相当活跃,他们多次遣使至宋朝朝贡,也与东北方的辽朝通好,同时联络各方势力,相互声援,对抗西夏的统治。我们在文献中,可以见到“沙州北亭可汗王”、“沙州镇王子”等称号{2}。据《宋史》等史书记载: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沙州镇王子遣使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4]清人戴锡章在其编撰的《西夏纪》中进一步说明:“是年(1041年),沙州回鹘来侵,却之。”[5]这说明进攻沙州城的战斗确实发生了。今人钱伯泉先生在《回鹘在敦煌的历史》一文中提出:公元1030―1042年,西夏与沙州回鹘交替攻占沙州。公元1042年,沙州回鹘正式占领沙州并统治该地直到1146年[2]。钱伯泉这个论断未必完全准确,但至少能够说明沙州和瓜州在西夏前期有着不一样的历史。 第二,现有的学术成果,很少有将历史文献研究与西夏时期沙州和瓜州的石窟营造的具体状况紧密联系起来研究,因此,现有的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的时代划分和营造背景的研究通常笼统划入“西夏时期(1036―1227年)”。在这近两百年的“西夏时期”,瓜州和沙州的历史各有其不同变化,而这些历史变迁,又对石窟的营造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对瓜州和沙州西夏时期的历史做较为细致的梳理,找出对石窟营造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相关的各种文字记载,并将其与现存西夏石窟联系起来分析,方可得出更为可信的结论,以加深我们对这一时期瓜、沙地区石窟艺术的理解。
沙州在西夏统治前期,一直处于西夏与回鹘和其他周边势力的攻击或袭扰中,政局动荡,民生凋敝,商贸阻断,生产局限,难以展开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因此,这一时期敦煌莫高窟所见到的西夏艺术遗迹数量虽然不少,但基本都是对前代洞窟的重修或补绘,几乎没有规划完整的新开凿洞窟。根据敦煌研究院的统计,西夏时期重修?a绘的洞窟多达四十多个[6],如果加上一批在时间上与西夏时期(1036―1226年)重复的所谓“回鹘洞窟”(1030―1127年),洞窟数量则可多达八十个左右。但几乎都是耗时较短、费力不多的局部重绘壁画。这与沙州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是吻合的。这些重修补绘活动,既有西夏党项族人的参与,也有回鹘人、藏人和汉人留下的遗迹。如莫高窟第61窟本是五代时期曹氏家族修建的大型洞窟,西夏时在甬道壁上有一些补绘壁画,并有西夏文、汉文的双语题记。其中汉文为:“扫洒尼姑播?氏愿月明像”。西夏文题记由史金波、白滨翻译为“燃灯行愿者播?氏成明”[7]。史、白二人共记录翻译了莫高窟壁画上的西夏文题记45条,内容主要有“功德发愿文、供养人榜题和巡礼题款”[7]369。其中第65窟壁画上有大安十一年(1085)西夏文题记,其内容译为“甲丑年五月一日日?全凉州中【多】石搜寻治,沙州地界经来,我城圣宫沙满,为得福还利,已弃二座众宫沙,我法界一切有情,当皆共欢聚,迂于西方净土。”[7]369这则西夏文题记说明党项人在沙州的佛事活动除补绘壁画外,还有清除积沙等管理类活动,而且佛事活动的目的是往生西方净土。这反映了西夏人佛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往生佛国净土的愿望较普遍。另外一条有明确纪年的西夏文题记见于第444窟,内容为“永安二年(1099年)四月八日日心……七……佛……上……”[7]381此题记虽然残破尤甚,但具体年代和日期清楚。这个“四月八日”是释迦牟尼诞辰日,说明西夏人在佛诞日是要举行纪念活动的。其他莫高窟现存没有明确纪年的西夏文题记也基本上记述相似的内容{1}。
西夏对瓜州的统治比对敦煌的统治要稳固得多。从西夏建国初年起就在瓜州设立了监军司,是全国十二个监军司之一,驻有常备军队,与沙州回鹘及其他周边势力的争斗,主要是由瓜州监军司的驻防军执行的。西夏对瓜州的有效统治管理,使地方形势相对稳定,经济民生得以发展,人口增加,并逐渐成为西夏政权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在李仁寿(夏仁宗)统治时期(1139―1193),瓜州几乎成为了这个皇帝的朝廷所在地{2}。这就为瓜州成为“西夏原创洞窟”的诞生地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但是,在西夏政权的前半期,瓜州因为邻近沙州,受到沙州战事和其他方面的直接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局限的。而且西夏国整体的政经形势,也对瓜、沙地区的历史有重大影响,举例如下:
(一)公元1082年,西夏实际统治者梁太后“自三月中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岭及甘、肃、瓜、沙州民,十人发九,齐赴兴州,议大举”[8]。中央政府把90%的瓜、沙地区民夫征调出征,显然会严重影响当年农业生产和商贸活动,也使佛教石窟营建活动无法展开。
(二)公元1093年,西夏“以兵备于阗。于阗东界吐蕃,与瓜州接壤。是时入贡中朝,请率兵讨夏国。梁氏闻之,令瓜、沙诸州严兵为备。”[8]335梁太后下令瓜、沙地区军民备战于阗,必定会使其他如开窟造像之类的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三)公元1097年,北宋朝廷收到报告:“(黑汗王)进奉人罗忽都卢麦译到黑汗王子言:‘缅药家(指西夏)作过,别无报效,已差人马攻甘、沙、肃三州。’……朝廷甚喜……若能破三城,必更厚待。”[9]《宋史》卷17“哲宗本纪”,则明确记为:于阗“破甘、沙、肃三州”[4]346-349。这场黑汗王朝与西夏的局部战争,没有提到瓜州,估计西夏军是以瓜州为基地出击。但甘、沙、肃三州都是近邻,整个河西走廊西段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四)公元1110年,秋九月,“瓜、沙、肃三州饥……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水草乏绝,赤地数百里,牛羊无所食,蕃民流亡者甚众。监军司以闻,乾顺命发灵、夏诸州粟赈之。”[8]369-370这场大旱灾,对瓜、沙二州及邻近的肃州都是灾难性的,导致了本地人口大量外流,这对本地经济的影响应是深远的。在这种形势下,要做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上历史记载表明,在西夏统治瓜、沙地区的前半期,该地区的政治局势不稳,经济民生发展缓慢,很难展开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尤其是沙州地区,经常处于周边各种势力的争夺冲突中,时而被沙州回鹘占领,又被黑汗王朝军队攻破,没有长久和平时期,故无法正式的规划开凿新窟。尽管沙州回鹘和沙州归义军残余势力都信仰佛教,也有意愿弘扬佛教艺术,许愿供养,但动乱的时局,并不容许大型开窟造像活动的发生。因此,我们在敦煌莫高窟只能看到重修前代洞窟、补绘壁画的痕迹。却没有见到真正完整意义上的西夏石窟。瓜州作为西夏的十二监军司之一,驻有重兵,局势相对稳定,人口也应该比沙州要多,经济基础更为雄厚,具备一定的开窟造像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但其毕竟受到周边局势的影响,军民忙于征战,人口流动性大,正式规划修建新洞窟的可能性也不大。
二 瓜州西夏原创石窟的营建
公元1139年,年仅16岁的李仁孝登基成为西夏王朝的第五位皇帝,开始了他长达54年的统治,是为夏仁宗时期(1139―1193)。公元1125年,随着西夏长期的劲敌辽国的灭亡,西夏国采取了依附新兴起的金国以换取长期和平发展的策略,并接收了灭亡的辽国故地西北诸州,还向金国求得了一部分地区。 ??《西夏书事》卷36记载:“夏人庆三年(1146)春正月,(西夏遣)使贺金正旦及万寿节。金以边地赐……乾顺又得辽西北诸州及陕西北鄙,其地益广。时仁孝又使人至金乞地,金主以德威城、定边军等沿边地赐之。”[8]415-416据这段史料,我们知道西夏国是在辽朝灭亡之后奉行了与金朝交好的政策,并拥有部分辽朝故地,沙州以西的伊州(今新疆哈密)也纳入了西夏版图,还从金朝乞得部分土地,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时期。公元1146年之后,瓜、沙地区不再有战争,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得以发展。瓜、沙二州逐渐发展成为西夏境内的发达地区之一,并成了西夏国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人提出:“至1165年之时,西夏仁宗皇帝李仁孝还亲临瓜、沙地区。”[3]75虽然这个仁宗皇帝亲临瓜、沙的事件还有待更多的史料加以证实,但瓜、沙地区在夏仁宗时已经成为与东部灵夏中心相对应的区域中心应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而且夏仁宗应该是对瓜州情有独钟,有可能曾经带着宫内宿卫官兵和国师等亲宠随从到过此地,并在榆林窟等地开窟造像。我们在瓜州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现存洞窟壁画中,仍可见到一些他们当年从事佛事活动的证据。
西夏专家史金波、白滨在榆林窟的16个洞窟中,共找到了47条西夏文题记。这些题记总共包含了841个字,内容可分为三类,即供养人榜题、发愿文、巡礼题款[7]378。仔细检索分析这批珍贵题记资料,我们注意到一些极为有用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夏仁宗皇帝可能在瓜州榆林窟逗留并从事佛事活动的情况:
第15窟题记:
南方?^普梅那国番天子
国王大臣官律菩萨二…
…当为修福
写……?…病
写…?夜?与[7]382
这五行题记,讲的应该是某日夜,皇帝生病,大臣官员为其写经祈福,祝愿其早日康复。这里的“南方?^普梅那国”就是西夏国,这个“番天子”就是西夏国皇帝[7]372。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肯定这个生病的西夏国皇帝就是夏仁宗,但皇帝夜晚生病,大臣官员马上知道并举办抄写经文仪式为他祈福,应该是大家一起住在瓜州行宫,或者就住在榆林窟前,才有可能做到。据前文知,夏仁宗是唯一被记载曾经以瓜、沙为活动中心的西夏皇帝,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组西夏文题记里记载的“番天子”就是夏仁宗。
第25窟西夏文题记众多,其中有提到“拜君”二字,又提到“圣恩思佛…塔亦疾早愿行…造玉瑞圣”[7]383。这里的“造玉瑞圣”有可能是指用玉造皇帝像,以求圣疾早去,天降祥瑞。另外,题记又提到有“男女一百余/时彼岸…果证…故大乘忏悔……因/供养……做令以此善根取当今/圣帝王座如桂如当全神寿万随身”[7]383。显然,这是官僚及其眷属一百多人为当今皇帝祈福,祝愿其长寿,得“神寿万随身”。同窟题记里再次提到“圣帝、大官”,并有“…丑年中正月二……瓜州监军……/子瓜州监军司通判赵祖玉”题记,这个“…丑年”据研究是夏仁宗时期的“癸丑年”,即1193年[10]。那么,题记里提到的“当今圣帝”或“圣帝”就是夏仁宗李仁孝。而“大官”则应该是瓜州监军司最高长官,其名字已看不清楚。
更加有力的证据见于供养人题记保存较为完好的第29窟。该窟供养人像前画了一位西夏高僧,题名为“真义国师昔毕智海”(图1)[7]383。这个姓昔毕的西夏国师亲自来主持第29窟内供养仪式,他应该是随仁宗皇帝一起来到瓜州的。而且该窟的主要供养人几乎都是瓜州、沙州的军事、行政高官,包括皇帝的侍卫统领兼史官向赵{1}。国师是西夏国僧侣的最高级称谓,国师一般随侍皇帝左右,常给皇帝提供咨询,国师昔毕智海和宫廷侍卫长兼史官向赵在榆林窟的出现,也表明仁宗皇帝有可能来到了瓜州。
由于夏仁宗时期西夏国政经形势总体稳定,而仁宗皇帝重视瓜、沙地区的发展,可能亲自来到瓜州居住并做法事,带来了西夏首都高度发达亦趋成熟的艺术。除国师、高僧等宗教界上层人士外,可能也带来了宫廷画师。榆林窟新开凿绘制的洞窟,如第2、3、29等窟应该就是此时修建的。这批洞窟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与前代洞窟大异其趣,展示了西夏成熟期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是我们研究西夏宗教、艺术、文化的珍贵材料。
三 敦煌、瓜州西夏石窟艺术的比较
敦煌在夏仁宗统治期之前,是回鹘人、汉族归义军残部和西夏军队拉锯争夺的地区。三方势力都信仰佛教,但在当地历史更长的回鹘人和汉人更有制作佛教艺术的动力和经验,因此,在敦煌莫高窟继续制作佛教艺术者主要是回鹘人和汉人,我们在莫高窟这一时期的壁画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特点。
随着敦煌地方历史研究的推进,刘玉权先生对西夏时期的瓜、沙地区石窟做了新的分期研究,从原划分为西夏的80余个洞窟中划分出来了23个沙州回鹘政权所修建的洞窟,其中莫高窟16个。这23个回鹘洞窟中,有13个洞窟绘有回鹘供养人画像,其中绘有回鹘王、王妃、王子供养像的洞窟就有6个[11],证实了回鹘人是这个时期佛教艺术的主要供养人。回鹘王和王妃的供养画像都画在洞窟甬道的两壁,这是唐、五代以来画窟主和主要供养人画像的位置。回鹘王和王妃的供养画像绘在这个位置,说明他们主要继承了归义军时期莫高窟佛教艺术的旧有传统。但是,这些洞窟的艺术风格和洞窟中所绘的回鹘王、王妃、王子以及侍从的供养人画像的人物造型、衣冠服饰都与高昌石窟、北庭寺院中的壁画风格、供养人画像十分相似,其回鹘族艺术的民族特征也是很明显的。
莫高窟第409窟东壁绘有回鹘王供养像,头戴桃形云缕冠,身穿圆领窄袖团龙袍,腰束革带,上垂解结锥、短刀、火镰、荷包等物件,脚穿白色毡靴,手执香炉礼佛。回鹘王身旁立一少年,其穿着打扮与王相同,应是王子。回鹘王身后侍从八人,分别为其张伞盖、执扇、捧弓箭、举宝剑、执金瓜、背剑牌。侍从均穿圆领窄袖袍,上饰三瓣或四瓣小花,束腰带(图2)。这幅保存完整的《回鹘王礼佛图》,为西夏时期莫高窟的佛教艺术供养人主要是回鹘人提供了重要证据。 此窟?|壁回鹘王的对面,画《回鹘王妃礼佛图》(图3)。王妃们头戴桃形金凤冠,头发间插花钗,身穿窄袖翻领长袍,手执花束。这是典型的回鹘贵族妇女装束,与汉族和党项族妇女的头冠、服饰有明显的区别。
西夏时期,敦煌莫高窟重绘了大量前代洞窟,重绘者既有回鹘人,也有当地的汉人和新来的党项人。各族势力之间既有武力争斗,也有和平相处,甚至相互通婚者{1}。总的来看,敦煌莫高窟西夏时期的艺术具备如下特点:
(一)佛教艺术品的制作数量较大,但基本都是在前人修建的洞窟里修补重绘,没有开凿新窟{2}。因此,这些由回鹘人、汉人和西夏党项人制作的佛教艺术品主要是以礼佛供养为目的,也就是作“功德”,为死后进入极乐世界作准备。
(二)艺术题材较为简明,窟顶主要绘团花图案(图4)和龙、凤藻井(图5),四壁则以贤劫千佛{3}或菩萨像为主(图6),经变题材则有简单的西方净土变(图7)、药师经变、观音经变等[12],也主要是前代壁画题材的延续,并无明显创新。
(三)艺术风格主要是延续敦煌中、晚唐壁画开始流行的大面积绿色基调,辅以红色线条,实际是前代归义军曹氏画院的风格。估计敦煌当地的画家在西夏攻陷沙州后,继续在为回鹘人、汉人和党项人工作,绘制佛教壁画,所以画法也没多大的变化。
瓜州现存西夏时期的洞窟主要集中在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其中榆林窟的西夏洞窟保存最完好。这里,我们主要以榆林窟的西夏窟来与同期的敦煌莫高窟略作比较,以说明瓜沙西夏石窟艺术的异同。
榆林窟西夏洞窟现存有4个,即第2、3、10、29窟[6]204-221。其中第2、3窟位于崖壁底层,进出方便。此二窟相邻,内容相关,应该是同时规划建造的。其内容之丰富、艺术水准之高超,堪称西夏石窟艺术之典范,很有可能是夏仁宗从首都带来的国师及高僧设计建造的,有西夏宫廷画师参与绘制完成的。而第29窟则位于较偏远的崖面,这个特殊位置的选择,可能与其用于特殊的供养仪式有关。第10窟损毁严重,难以详论。
当我们把建造绘制时期大致相同的榆林窟夏仁宗时期的三个洞窟放到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可以看到如下特征:
(一)此西夏三窟的建筑形制完全一致,均是方形平面窟,覆斗顶,中心部位设坛,坛上塑像。这种标准化的建筑式样,可能与西夏流行的一种名为“烧施”的法事活动有关。榆林窟第2、3、29窟窟内壁画都有明显的烟熏火燎的痕迹(图8),应该就是在窟内多次举办烧施法会的结果。特别是第29窟,窟内壁画烟熏状况非常严重,可能是多次举办烧施法会造成的,而且该窟壁画中有描绘西夏国师主持烧施法会的画面,更为直接地表明了此窟主要用于举办烧施法会的实用功能{1}。
(二)榆林窟西夏三窟壁画的题材有许多共通之处,既有经过整合的西夏佛教特色题材,又有汉地佛教的流行内容,也有藏传佛教内容,是夏、汉、藏三合一的题材,反映了西夏仁宗时期折中的宗教信仰和图像构成特征。
(三)榆林窟西夏三窟的艺术风格也表现出夏、汉、藏三个艺术传统兼容并存的特征。以第3窟壁画为例,左右两壁上的净土变是典型的西夏风格,净土里的水池变得很小,大片的绿色草地取代了原来的“八功德水”,反映了草原民族对草地的喜爱(图9)。而窟门两侧的文殊变和普贤变则采用了汉地流行的画法,特别是背景山水以水墨为主,反映出南宋院体山水画的明显特征(图10)。而窟顶和净土变两侧的壁画则是明显的藏传佛教画风格(图11)。这种夏、汉、藏三种传统并存的艺术风格特点,与夏仁宗时期的宗教文化特征是相吻合的。
夏仁宗李仁孝的生母是汉人曹氏,仁宗即位后,尊其母曹氏为国母,与其庶母任氏并立为太后。仁宗之妻罔氏皇后虽是党项人,但对汉文化极为喜爱遵从。李仁孝即位后,于公元1144年5月遣使赴宋朝,向宋朝献珠玉、金带、绫罗、纱布、马匹等物,恢复了与宋朝中断了近二十年的使节往来。又在夏国内各州县设立学校,教授儒学,甚至在皇宫中设立小学,置教授,还与皇后一道亲自给学生讲课。公元1146年,李仁孝模仿宋朝制度,建立太学,又尊孔子为文宣帝。公元1161年,李仁孝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为学士,又命王佥掌管国史,纂修《李氏实录》。总之,在夏仁宗时期,以宋朝为楷模的汉文化传统在西夏被趋之若鹜。
公元1159年,夏仁宗派使者到西藏,奉迎噶玛噶举教派始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赍经像到凉州,被奉为上师,并组织人力大规模翻译他带来的佛经。估计格西藏琐布带来的藏传风格佛教画也开始在西夏流行开来,因此,许多佛教艺术家都以1159年为上限来判定西夏藏风佛教画的制作时间[15]。虽然有学者撰文对以1159年为上限给西夏藏风佛教画断代提出质疑,认为有些西夏藏风佛画制作时间应该更早[13],但用1159年藏传佛教画开始流行于西夏,特别是皇家寺院的记载来比对瓜州榆林窟的西夏壁画,其时代特征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们把瓜州榆林窟的三个西夏洞窟,即第2、3、29窟的营造时间定在1159年至1193年这段时间内应该是合理的。而且,此三个洞窟的建筑形制、壁画内容、艺术风格也有明显的一致性,其建造时间应该是大致相同的。
总之,西夏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与瓜州同期石窟明显不同:敦煌主要是继承前代石窟壁画的题材和风格,很少创新;瓜州则修建了一批形制独特、内容新奇、风格?异的原创新窟,集中展示了西夏石窟艺术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