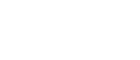中图分类号:J97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3-0179-05
1942年发牛在中原地区的饥荒使黄河两岸
数百万人死于饥饿。由白修德报道、福尔曼拍摄的河南灾民图像70年后在河南博物院展出。这些照片小是艺术作品,也不是艺术摄影,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幸存者也大都死去,这些照片还是不肯变成艺术,它是历史、真实和记忆。这些照片拒绝变形,拒绝任何艺术性的观看。它记录和书写历史,直接与外部历史链接。就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真实关系而言,这些图像是再现,不是变形,甚至也不是表现。这些灾民图像没有摄影者的主观性,没有艺术的意识和任何表现主义色彩,它固执地成为见证――在灾难面前,在人道主义灾难面前,它的拍摄者放弃了艺术,执着地成为见证。然而这些沉默着的图像却有着多重的威力。
照片不运动,它凝固在一个瞬间,一个死亡的瞬问,一个灾难瞬间。图像不流动,不叙述故事,它让人凝视。图像静止,凝滞不动,因此才有可能让站在它们面前的人凝视、凝神、沉思。照片凝滞,照片孤独,像一个个单词,而非句子,照片不运动,不产生故事,不产生叙事。照片不开始,也不结束,你可以一卣凝视下去,直到观看者自身无力承受。图像不叙述,因而她们没有名字,没有家,没有一切。她们仅有的,是饥饿、疾病、挣扎、无助、死亡。这些名词和形容词,直接记录在这些躯体上,铭刻在这些面孔上,成为无声的言语。
这些足可见的事实,它在沉默着,可见物在固执地沉默着,它却又将可见的与可说的链接起来。如果可见物唤起了可说的,一是质询这些照片意味着什么?发生了什么?他们遭遇了什么?这是新闻图像要告诉人们的真相;还有一种可说的也将要被唤醒,它意味着一种“文学性”的质询:照片卜的人们、死去和濒临死亡的人是准?她和他叫什么?他们的家在哪里、她们的家人在哪里?
图像上的死者或濒临死亡状态的人,除了“群众”一样无法区分地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些孤单的个体仿佛他们和世界的一切关系都被饥饿与死亡解开了但我们知道他是儿子、是父亲、是丈夫;她是母亲、是女人、是妻子或者姐妹。然而,饥饿和死亡解开了人与他人之间的任何关系,她或他根本不再处在这些亲密关系之中,不再处在人类社会关系之中。饥饿与死亡使每个人都孤零零的,使每个人都归于孤立无援,置身于绝望无助之中。在20世纪,即使在战争状态中,在整体上经济技术和新闻媒介得到巨大发展的时代,饥饿与死亡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图像所显示的静止、停滞、孤立,意味着几乎所有人类关系的解除,意味着亲密关系或家庭关系的解开,否则,他们不会作为儿子而死,不会作为父亲而死,不会作为女儿而死,不会作为妻子和母亲而死,最终,如果人类社会存在着的话,他们不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而死。这一亲密关系和人类伦理关系决定了他们会得到拯救,他们会得到社会的援手。这些孤立的图像是一切人类关系的解开的一个直观表象。
铭刻在这些死者躯体或濒死者面孔上的不仅是饥荒与死亡,而且是社会关系的解开和人类社会的消失,孤立无援更加深刻地书写在死者的脸、眼睛和躯体上,书写在他们的处境中。照片记录的不仅是他们的饥饿,还有他们的绝望,他们的无声无息。图像的孤独意味着灾民群体与社会没有了关系,与国家与政权没有了关系。灾民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似乎被解除了。
这些静止的图像里,有着白修德和福尔曼在场的眼睛――如今已经闭上的眼睛,这双摄影之眼对于中国观众才刚刚睁开,在这双见证之眼后面没有任何艺术的趣味,然而,事实上,白修德和福尔曼的眼睛后面隐含着文学艺术所培育的看待人类的方式,观察这些现场并拍摄了图像的眼睛显然是一双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的眼睛。唯有人文主义之眼,才能如此“关注”他人的苦难,凝视他者的脸,关切他人的处境,记录和表达他人的生存之痛,并被这种超越了人类伦理底线的痛苦所激怒。是他们,把这些图片交给了最高当政者,让他身体发抖,并最终给予了幸存者以救助。灾民没有等来政府,也没有等来神仙,他们在不幸之中所幸等来了一双见证与摄影之眼。
图像并不讲述故事,然而,这些图像并非完全不可感知,不可命名,不可句子化或进入叙事句法。从图像所表达的可见物开始,从可见物与可说物的连接开始,电影《一九四二》就在试图回应一种可说的,于是有了叙事虚构。这里的虚构不是指对真实的偏离或歪曲,不是指本片纯属虚构或想象,虚构意味着汇聚起丢失的记忆,丢失的真实:这些照片上的人,没有姓名、没有家园、没有亲人的男男女女,在电影的叙事虚构中,重新拥有了一个姓名、一个故事、一种社会境遇和个人遭际。虚构是从细节上的可见物转向细节上、情节上的可说物的一种“补充的在场”。
在这里,想象他人,想象生与死的细节与情节,想象他人的故事,这一文学性的或美学的“好奇心”,与对他者的伦理关切一致了起来,当然,这里指的是在动机卜.的一致性。而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美学的观看与伦理关切之间,依然存在着微妙的却并非不重要的差异?这些图片有一些故事,而图像中的人们却没有故事,连社会记忆也极其模糊了。或许这是因为,在这场灾难里没有英雄,甚至连敌人也没有。准造成了他们的苦难?即使“准”不意味着一个可见的人和唯一的原因,责任也依然存在,就像后果存在着一样。没有英雄的苦难,总像是无意义似的无人言说。因为无意义,因而一直陷入沉默。照片不运动,它们停止在1943年的某个瞬问,然而这些图像并不是简单的现实,这些图像是“可见物与可说物”之间的一些关系,是一些“之前”和“之后”的昭示,是多重原因和一个无法改变的后果之间一个瞬问最悲剧的凝定现实。 刘震云的报告文学《温故一九四二》中如此
描写:“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1]这是刘震云在采访、写作《温故一九四二》之初和他姥姥之间的对话,他把这些记录在了报告文学的开头部分,看似平静的回答读起来却有着揭开淹没记忆的隐秘痛楚。或许正如刘震云后来所说:“当死亡变的像家常便饭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遗忘就不仅仅是一个记忆的问题,而它会成为一个态度。”
灾荒的残酷和历史的荒蛮感触动了冯小刚,耗费19年和遭受多次审查、冷遇、挫折后拍摄完成了这部作品。冯小刚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如此回答:“多灾多难就应该不回过头去,就把眼睛蒙上不去看,怕提起,我觉得它不是那样的关系。你经历了这么多灾难,你只有不断地反省这个,让人们不要忘了这些灾难。它才能再次面对这灾难的时候,人们冈为这些作品想到了过去那种他可能会有一些自觉减少这样灾难的发生。”作为中同大陆首位作品总票房过10亿的导演,在《一九四二》的拍摄中,他试图对这一民族苦难进行一次影像化的、全景式展现。
刘震云的历史报告文学《温故一几四二》以记录方式、众多叙述线索讲述了这一历史。在此意义上,《温故一九四二》的叙事更接近福尔曼的图像记录,在每一个体、每一幅照片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故事,而不是只有一个连续性的故事,图像表达的是无数故事的沉默的碎片。每一幅照片本身都隐含着故事的痕迹,唤起可说物与可见物的多重链接。而熟知平民趣味的冯小刚则将一段沉蕈的社会记忆缩减在一部情节剧之中,删除了纷繁复杂的叙事和多重叙述线索,将焦距对焦在一个家族,完成了常见的关于家园毁灭的故事建构。应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阶段冯小刚已经熟练掌握了借鉴好莱坞类型电影模式,打造中国式影像美学的兼容之道,探索出了美学和商业有机杂糅的新视野。投资2.1亿元的《一九四二》在技术层面上完全能够媲美好莱坞的史诗效果,视觉特效呈现的逃荒的场景、航拍的爆炸场面、灾民跳火车的实拍镜头和大场面成千f二万群众演员的凋度在视觉效果上都堪称优质。摄影家吕乐为影片设计的灯火余烬般的灰暗的画面风格,叶锦添为逃荒难民设计的服装造型都为影像呈现了真实观感。
影片在时空没计上紧扣逃荒路线,以一种全知视角的经典现实主义模式,叙述老东家范殿元一家在逃荒路上家破人亡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这足一种既接近中同古代戏剧模式又近似于经典好莱坞式的叙述模式,围绕主要人物及其家族命运的展示,影片突显出一种个体命运及其故事,而历史事件实际上成了家族故事的历史背景。或许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最为看重的是人伦关系,因此这一类型的中国电影最为观众熟悉,创作上较容易把握,对于导演具有票房价值和艺术感染的双重诱惑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家庭人伦的展现已经形成了中国影戏传统的丰要部分。如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和蔡楚生的《都市的早晨》《渔光曲》。这些传统电影尽管是以家庭的悲欢离合为自足点,却企图能够与当时的广阔社会背景的展现有机融合,展开社会批判的多维层次。《一九四二》尽管出于情节剧的需要,有了叙事和结构上的情节化的集中与化约,影片还是力图建构一个多层次的叙述。老东家和长工两个家庭成为一条叙事线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官员、军队的救灾态度是另一条线索,其中以《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灾区所见所闻的一切进行了文献性的串接。
显然,电影《一九四二》的编导看到并使用了福尔曼所拍摄的这些灾区与灾民图像,这些痕迹反映在电影中人物的着装、面相、身躯、随身携带的器物等方而,然而与原初的新闻图像相比,被表演的图像、被“复现”的故事,在回应可说之物时显然降低了可见物的凝视效果。电影的运动影像并非仪仪是为静止的图像进行故事化的编码,电影是让沉默说话的一种形式。从静止的凝固的图像形式转向运动影像,电影一方面对写在图像中面孔上或物品上的“故事”的可读性或可说性证据进行解读,也将可说物转向可见物,与1943年到达灾区的白修德和福尔曼所拍摄的灾民图像相比,电影要将图像中的沉默转化为叙事行为。这是从一种再现体制向另一种再现体制的转换。这一叙事行为意味着要转移和偏离图像所凝定的那一瞬问,转向图像定格瞬问之前和之后的状况。
《一九四二》在叙述方式一主要基于一种情节剧模式,以表现家庭人伦悲欢离合的故事来透视社会与人生,尽可能遵守着人物、故事场景和命运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法则。影片第一个场景是老东家范殿元所处的延津的村庄,灾荒之前他家境殷实、儿女双全,而在灾民前来抢粮却遭遇飞来横祸,唯一的儿子被打死。第二个场景是被迫弃家逃荒的途中,亲眼目睹儿媳、老伴、孙子一家亲人的种种惨死,女儿被卖掉;另一条线索址是长工瞎鹿、栓柱等人的惨死,以老东家的家庭遭遇呈现和折射出三百万灾民的苦难缩影。第三个场景是影片结尾处孑然一身的老东家,认领了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女孩,力图重新给人以生的希望。
不难看出,《一九四二年》在对传统电影典型家庭伦常模式的承继中,在情节剧的模式之外,力图展示多层次的叙事维度,突显一种社会批判意识 1942年的河南是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这场人饥荒死亡人数几乎达到官方统计的中国军队抗战中死亡人数总和,这个事实本身已不乏悲剧性的张力。但冯小刚在历史认知、多线索叙述和图像意义的揭示上还显得不够从容或缺乏自信。影片既想以情节剧的方式突出一个家族的故事,又显示出抹平主要角色的历史直觉,力图使每一个角色都有着特殊的叙事功能,构建一个多线索的戏剧场景。然而,冯小刚在多重叙事、大量历史事件的并置和情节剧之问显得犹疑,使影片无法摆脱情节需要的主导:张涵予饰演的牧师角色,除了有着冯氏笑料外,其宗教救赎功能和对主题的表现显得可有可无;好莱坞演员蒂姆?罗宾逊饰演的意大利火主教神父角色在叙事上儿乎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情节剧的结构,偶然出场的白修德也失去了更多的叙述功能;影片开始与结尾时的画外音叙述,由于既未能清晰地显现出叙述者的身份也未能贯穿故事,实际上失去了有意味的讲述功能,唯有几处使用对比蒙太奇姓露非线性叙事或并列图像的端倪:饥饿的灾民打劫老财主范殿元家死伤的惨状和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第一次出场的饭局镜头构成对比蒙太奇;灾民们开始逃荒路、生死未卜的镜头与白修德在重庆美国大使馆初见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时歌舞升平场面的对比蒙太奇。还有几处以“吃”所进行的蒙太奇连接,李培基第一次出场,厨师精心烹制的鲤鱼焙面的特写镜头(鱼肉符号意味似乎太明显了);蒋介石第一次出场也是和灾区混乱现实构成对比,以特写蒋拨开鸡蛋的动作进行连接、转场 在这些细节上,导演对饥荒灾难核心的“吃”的问题进了暗示,似乎一方的“吃”正是另一方饥饿的原因,但这种蒙太奇式的聚焦和批判性对于“饥荒”问题带米的灾难始终缺乏深刻的说服力。 情节剧总是无法拒绝“艺术”的诱惑,即强调人物、故事和命运连续性与统一性的叙述模式的诱惑。与图像的命运相比,运动影像的连续性优势也成为一种缺陷,一方面,当运动影像取代了图像的非连续性与孤立性之时,运动影像丧失了让人凝视的功能,其实这并非小能得到一些弥补,在雷乃的《夜与雾》中,一双惊恐的眼睛、一张脸,一个突然放大并定格的图像,一再地重复性地出现在它的叙述之中,不仅创造了叙事的某种节奏,也强调了凝视。对死者、对他者、对眼睛的对视,接受一双眼睛的凝视,就是接受一种社会伦理的质询接受一种人类道德或人类关系的质疑。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图像所显示的灾民的孤立状况,当情节剧模式陷入家族故事的套路之中时,无形中削弱了福尔曼的摄影图像所显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解除这一真实处境。在影片让人关注一个家族的命运对,多少也削弱了观众对灾难群体的关注。事实上,在情节剧之外,灾难的特性恰恰在于它没有主角,没有主要人物,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一方,每个人都是故事的一个枝节,没有任何人是主要人物,没有任何人能够贯穿故事的始终。
显然,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未能对饥荒完成一次有感染力的表述,而草草地以一个与死亡对立的意象,以“生”的开放式的暗示结束,老东家停在小女孩身边说:“你叫一声‘爷爷’,咱们爷俩就算认识了。”孩子仰起流泪的脸喊:“爷。”冯小刚解释说,“这是一个在黑暗中、在绝望中的两个人和世界的和解”。但这仅仅是角色和导演本人心中的幻想和解。沉淀在社会记忆中的黑暗与绝望远不止期待着一种戏剧性的和解。事实上,这一灾难的名称不是饥饿,而是人类关系的缺乏,是社会伦理及其制度形态的缺乏。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福尔曼最早报道了河南1942年灾情,正是由于他们的报道使河南灾民得到国民政府的救灾援助,影片中也出现了与此相关的细节。但在1978年白修德试图把他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整理成书时却发现,“当我试图从过去的笔记中认识这场大灾时,其中生动形象和有感情色彩的东西越来越少,理性分析和数字统计越来越多”[2]。他恍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这段悲剧时间间距变长,他记忆中活生生的灾民开始变成了冰冷的数据。对这样一个亲历者来说,他悲哀地感受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被风干了,记忆失去了它的生动性和感情色彩,或许还失去了它的道德价值和推动人类社会的那种伦理力量。白修德对历史残酷性和个人记忆形态之间关系的反思似乎值得我们深思。历史学的声音无法替代亲历者或者幸存者的声音。基于数据的历史学话语和亲历者的情感记忆话语,都是历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
就历史事件的再现而言,使用“生动形象和有感情色彩”的表现方式是影像艺术的特殊授权。影片《一九四二》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灾荒的残酷和社会的荒蛮感,尤其是对灾难场景的展现有着如此大场面的铺陈,不断用大型的灾难画面来提醒观众这是怎样的一幕悲剧,影片中的灾民抢粮的打斗和杀戮镜头,日军轰炸中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的场景、野狗争食尸体内脏的惨状,以及强调记者白修德和福尔曼对灾民尸体的拉近、定格、拍摄的镜头……但当这一切落人导演预设的叙述模式时,维系于情节剧之上的这些影像内容却并没有获得审视社会悲剧与破解历史之谜的能力,感官上的灾难景象并未能触发观众对社会的思考,或唤醒创伤记忆的应有的历史想象力。情节剧的俗套减弱了历史真实感,也弱化了艺术感染力,从而未能带给观众应有的情感冲击和认知共鸣。在某种意义上,情节剧的煽情式表现犹如新闻报道话语中的陈词滥调,正如当时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使用的“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致使蒋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著名电影媒体《好莱坞报道》的评论也给出了一种批评声音:“如果对这段历史没有较多的丫解,西方观众会在两个半小时的观影中感到疲劳。”[3]《一九四二》北美地区的票房总额为10万美元或许也是一个注脚。不明历史原委、看不懂中国式情节剧的观众会将其视为一个可怕的故事。
毋庸讳言,多次审查的冷遇使冯小刚意识到了一九四二“这个惨烈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政治伤口和敏感性历史观话题”,诸如影片中的李培基被塑造成了一个为民请命、兢兢业业的形象,这和现实中1941年李曾向国民政府瞒报灾情的真实形象有相当大的差距;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政治上的各种矛盾和救灾不力的诸多情况也远比影片中的单线条叙事所展现的更为复杂。这或许也迫使冯小刚的影片游走于审查体制和商业动机的夹缝之中,冯小刚曾在影片公映前这样解释拍摄《一九四二》的初衷:“记住历史,重新发现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它的重演。”不可否认,正是这部影片让一直尘封、鲜有问津的历史浮出水面,使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社会记忆提到公众记忆层面。或许这也是一种策略:“只提出问题,不试图僭越历史和他人来回答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只需要记住。”但影片的问题恰恰在于它失去了提出问题的维度,灾难情境的铺陈难以弥补历史思考方面的不足。
对于艺术作品而言,提出问题往往比回答问题更符合艺术的特性,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任何哪怕只审视不解释的作品也通过自身的叙事架构充当了历史的解释者。因此,问题或许是,情节剧的叙述框架与再现大规模历史事件所需要的结构之间的断裂或不吻合。在情节剧的叙述模式里,有着主要人物及其命运线的表现,但事实卜^在大饥荒和几百万人的逃荒途中,没有人是主角,而且恰恰是因为整个历史事件中没有主要人物才会悲惨至此;在情节剧的叙事中,一个家族显现了一种故事的轮廓,一种“命运”的形象似乎出现r,然而在这场大灾难中,一切故事与命运几乎在一开始就结束了;在情节剧的叙事里,主要人物的死亡成为悲剧时刻的顶峰,但事实又是,在经年累月的大饥荒中,死亡发生在任何一个时刻,死亡不再是悲剧的瞬间事件,就像刘震云所说的,“当死亡变的像家常便饭的时候”,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几乎平淡到没有了任何悲剧感。这意味着,对于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来说,死亡标志着一种悲剧性的时间结构,或悲剧性的时间焦点,但实际上,对于大规模的灾难与灾民群体而言,死亡标志的是一种日常性的时间,一种“家常便饭”式的时间。在此意义上,自修德和福尔曼的摄影图像似乎比电影说出了更多的真实。正如阿尔都塞在一篇批评情节剧的文章中听说:“根本的问题还在这里:有另一种时间结构,即‘悲剧’的时间结构,在同这种‘缓慢’的时间结构对立着。因为,悲剧的时间(尼娜出场――即戏剧中的女主人公)是充实的:几个瞬时动作构成了纽结,即‘戏剧性’时间。这段时间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从内部推动着它,自己产生出自己的内容,因而不可能没有故事发生。这是一种典型的辩证时间,它把另一种时间及其空间表现的结构一起取消。”[4](P128)由于历史叙事与情节剧之间产生的叙述话语的断裂,《一九四二》的内部结构也充斥着时间性的分裂,即悲剧性冲突的时间与日常性的平庸化时间,悲剧性的死亡与家常便饭式的死亡,出于情节剧的需要,影片企图强调悲剧性的时间与悲剧性的死亡;出于历史叙事的目的,影片再现了缓慢的时间和习以为常的死亡;出于情节剧的模式框架,影片设计了几个主要人物及其家族命运;出于历史再现的需要,影片以大规模的无名无姓的人群充当了背景与道具。问题却在于,前者减弱了后者应有的历史感和震撼力。 记录式的图像再现和电影再现是两种不同的再现体制,图像具有在场的原始威力,图像取消了任何方式的艺术中介物,消除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对于图像来说,除了原始记录之外,除了真实性之外,消除了所有的艺术操作、表演和预演,图像所表达的是一次偶然的遭遇,是一场境遇的记录。没有艺术的操作方式和意图闸释的工作,拍摄者的眼与心,拍摄者的感受、痛苦与愤怒,一切都隐藏在图像真实性之中。他们决不让这样一些主观性留在图像之中。图像消除了中介行为,也消除了中介方式。图像显现的是,现实与形式之间的直接同一性。、这里没有为艺术留下空间。然而当电影以运动影像的方式,以情节剧的方式给予图像所表达的内容以叙事时,电影就成为“拟像”行为,电影是以各种中介形式对真实的再现,因而这一再现体制与图像的再现体制有着巨大的差异。以“再现”或“模仿”为诗学原则的电影的运动影像,自然不是图像的原生在场,演员和表演成为电影叙事的中介或媒介如果说以叙述历史为己任,除了纪录片之外,电影的再现体制所遵循的是“相像”,而不可能是与原生在场之物的直接同一性。电影再现通过“相像”体制遵循现实性的原则图像是现实在场与形式的同一,而电影是相像的再生产电影叙事无法排除其艺术虚构的特性。作为再现,作为依赖中介物、依赖模仿即表演的艺术形式,电影对真实的再现就有了“相像的社会生产、非相像的艺术操作和症候的话语性”[5](P29)这样三个领域,电影游艺于这样三个不同的空间。电影能够做到的绝小是相像的礼会生产,而是相像与非相像之间的游艺。
或许,图像的原生在场同样也可以出现在以模仿为再现方式的叙事之流,用可以凝视的历史图像,暂时中断以表演为中介物的电影的运动图像,给予真实图像以片刻的停顿,以瞬间的凝视替代运动影像的轰炸;一种不煽情的、冷静的、多元并置的叙述方式;一种频繁发生重复发生的事件与独一无二事件之问的并置;一种人们受到煎熬的缓慢时间与瞬间性的短时段的并存;以更多的并置方式处理事件的多重线索,而不是刻意在情节剧范式中营造一种戏剧张力等等,这意味着,在情节剧叙述模式之外,以再现历史为主旨的电影叙事在形式上的其他可能性。正如郎西埃所说,这是一个所有故事都被分解的世界,所有故事被分解成句子的时代,这些“图像句子”可以与其他图像句子、声音、线条、话语进行交换或并置的时代,“它将年轻的电影艺术献给了一些相同的并列句”,在可说的与叫可见的之间也存在着蒙太奇式的剪辑,对此,郎西埃有着意味深长的表达:“而图像呢,它却变成了主动的威力,跳跃的放电威力,两种感官范畴之间体制变化的威力 图像句子是这两种功能的结合。它具有一种统一性,将人型并列的混沌力量二分为连续性的句子威力和断裂的形象化威力。”[5](P63)正是这一威力维系着可说的与可见的、图像与运动图像之间的艺术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