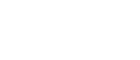中图文献号:C912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5.03.009
在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的形势下,如何让老年人幸福安度晚年正在成为重要话题。国内学者普遍致力于从总体上研究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编制幸福感量表 ,但由于影响幸福感的因素非常多,该范式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于是一些学者便开始专注某特定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这一范式又可分为公共服务决定论、生理机能决定论、社会结构决定论三大类。 两种研究范式达成了基本一致:传统养老很大程度上依靠亲属、邻里关系完成;城市老年人这类社会关系的断裂,造成养老困境的出现。但这一主题并没有得到持续关注, 除贺寨平[1]关于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与生存状态的研究外, 其余大多不成体系。研究者多认为“社会关系网”是农村地区的“保留品”, 依靠子女等社会关系养老的模式在城市中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无论农村还是城市,老年人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社会网络也并不仅仅是将老年人纳入“人情世故”的消极工具。相反,每个老年人有自己所构建的社会网络,以此来获得重要信息、积累社会资本并决定自己需要采取的行动[2]。社会网络的规模、成分组成等因素都会对老年人生活幸福感产生很大影响。
1 研究方法及设计
1.1 自变量及其测量方法
社会网络指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本研究认为,老年人社会网络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规模,社会网络组成成员的异质性,以及社会网络在老年人生活中发挥的均衡性作用将会对老年人幸福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三个主要变量:
(1)社会网络规模,即各部分社会网络中成员数量。该变量的获取需采用提名法对老年人社会网络进行调查,统计调查对象在每一种社会网络中提到的人数:一是情感支持,即与何人进行交谈、从何处获得心理支持。“当您难过时,您会找人诉苦吗?如果会,都能找到哪些人?”通过这一问题可以有效识别老年人社会网络中可以为其提供情感支持的人员;二是工具支持,“您一般都找哪些人来帮忙,比如搬重物,需要人照顾,或者需要生活费?”这一问题实际上包含了老年人生活“工具”的三个方面,即体力、劳务、资金支持;三是社会交往支持,“您空闲里都和谁一起活动呢,比如散步,聊天,打牌,下棋?”
(2)社会交往的异质性,用以测量老年人社会网络成员在某一方面的相似性。研究中将老年人社会网络结点按照年龄分为七组,60岁及以上分为一组,60岁以下每间隔10岁分为一组。在各个年龄段中,如果存在相应的网络结点,统一按一分计算,如果没有则不计分。这样,就可以得到从0到7分八个不同的得分,分数越高,异质性越强 。
(3)社会网络对老年人生活内容的均衡性影响, 即现有社会网络所形成的老年人生活结构。该变量获取需测量老年人日常时间安排:维持基本生活的时间--忙碌生活事务和睡眠;丰富生活的时间--参加活动和交谈;独处时间--独处,无所事事。计算三种时间在一天中所占的比例并将所得结果生成新的变量。
1.2 因变量及其测量方法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一般包括:认知评价,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即生活满意感;正性情感,包括诸如愉快、高兴、觉得生活有意义、精神饱满等情感体验;负性情感,包括忧虑、抑郁、孤独、厌烦、难受等情感体验[3]。总体幸福感量表(GWB)是为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定的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用来评价受试对幸福的陈述。本研究对其进行了两点修订:一是对GWB量表具体问卷进行了文化语境上的修改以适应中国老年人的语言习惯,如将“你是否正在受到或曾经受到任何约束、刺激或压力”改动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你是否感觉心情压抑”;二是出于研究需要将“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忧郁或愉快的心情、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六个维度进行调整,最终形成了本研究因变量的六个构成因子:对生活的兴趣和计划;对健康的信心;精力;愉快和松弛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自我接纳。做出调整后的问卷更适合老年人生活实际。
1.3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抽取青岛市1200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按照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分成两组,每种养老方式中各抽取男性与女性老年人60岁-70岁、70岁-80岁、80岁以上老人各100人。抽样以青岛市行政区划为标准分层进行。本次调查回收问卷1105份,剔除乱填、漏填问卷,实际有效问卷为1050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92.0%和87.5%。研究主要采用SPSS软件进行均值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假设检验。通过分析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明确社会网络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2 社会网络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我们将被测者社会网络成员数量作为总体均分,用以表示老年人社会网络的总体水平,并用社会网络各部分成员表示各因子水平。青岛市老年人社会网络平均规模为14.4人,情感支持(4.66)网络低于工具支持(4.98)和社会交往网络(5.77)。如表1所示:
表1 青岛市老年人社会网络基本情况
N 均分(M) 标准差(SD) 排序
工具支持 1050 4.98 0.36 3 情感支持 1050 4.66 0.48 2
社会交往 1050 5.77 0.62 1
2.1 社会网络规模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社会网络各个部分对幸福感各部分的影响,采用幸福感总体与六个维度和社会网络三个维度之间的7x3相关矩阵进行分析。如表所示:
表2 不同社会网络规模与幸福感六因子的相关性
幸福感 对生活的兴趣和计划 精力 愉快的心情 自我评价
和接纳 对健康
的信心 对情感和
行为的控制 幸福感
社会网络 工具支持 .193 .300 .421 -.532 -.401 .397 .352
情感支持 -.145 .321 .400 .270 .209 .356 .580
交往支持 .7300 .193 .645 .191 .580 .186 .579
2.1.1工具支持网络对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支持网可以定义为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个人可以利用周围的社会关系实现工具性目标。社会支持网有助于社会个体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和危机的解决,维持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青岛市老年人工具性网络规模总体较大,但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明显。如果将老年人按照居家养老和养老院养老进行分类比较,则可发现居家养老老年人的工具性支持网络规模相对较小,且工具性支持与这部分老年人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达到了.682,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说明工具性网络对不同养老方式下的老年人具有不同的影响。养老机构为老年人由于提供了集体生活的环境和专业服务,能在普遍水平上满足老年人搬重物、食宿、出行等方面的需求。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由于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因此工具性网络整体水平较低,有能力获得工具性支持的老年人自然处于较高的幸福感水平。
表3 不同养老方式下老年人工具性网络规模均值及其与幸福感的相关性
养老方式 均值 t sig 与幸福感相关性
工具性社会网络规模 居家养老 .382 -.535 .032 .682
养老院养老 .573 .328
2.1.2情感性网络对幸福感的影响:规模与深度
为深入研究情感性社会网络对幸福感的影响,我们对不同性别、不同养老方式下情感性社会网络与幸福感的相关性进行对比分析:
表4 不同性别、不同养老方式下情感性社会网络与幸福感的相关性
均值
相关系数 精力 对生活的兴趣和计划 愉快和轻松 自我评价
和接纳 对健康
的信心 对情感和
行为的控制 幸福感
家庭 3.7822 -.022 .461 -.162 .129 .424 .786 .382
养老院 3.7175 .193 .711 .887 .122 .201 .397 .391
男性 3.9215 .645 .321 .300 .270 .209 .356 .390
女性 4.8548 .215 .336 .128 .625 .572 .281 .387
可见,情感网络规模的扩大与老年人幸福感总体水平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然而情感性网络规模扩大有利于提高男性老年人精力,对女性则是提升自我评价。对不同养老方式的老年人说,情感网络有利于增强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但对“愉快和轻松”不利。而在养老院则相反,情感网络越大,越有利于轻松和愉快。家庭老人本身与四邻的关系较密切,本身情感交流网络成员相对较多,进行情感交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排解压力以避免行为失控,但交流过多则会得到过多“小道消息”,从而对精力、轻松愉快产生微弱不利影响。相比之下,养老院老人情感交流网络规模较小,受集体生活环境的限制很少单独交流情感,于是网络规模的扩大便会起到较强的“边际效应”。
然而仅从其规模上来测度情感性网络与幸福感的关系是不全面的,还应当从情感性网络的深度和“有无”方面考察。首先,从调查数据中检索出情感性网络缺失的老年人,发现其幸福感在自我控制以及自我接纳方面均值极低。其次,检索情感性网络规模为“1~2”的老年人对其幸福感得分进行分析,并与全部老人幸福感均值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在数值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从中可以推测情感性网络作为疏导情感的重要方式,本身并不需要很大的规模,而是需要深度。具有深度的情感交流渠道,即便规模不大,也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为验证这个假设,将老年人按照情感性社会网络规模得分情况分为两组:得分在1~2分之间的样本数据为一组,得分在2分以上的样本为一组。之后对老年人幸福感均值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发现并无明显区别 。
表5 情感性社会网络高、低两组老年人幸福感基本描述统计量
情感网络状况 N Mean Std.Deviation Std.Error Mean
幸福感均值 低规模 300 3.6678 2.3232 .22321
高规模 750 3.8712 2.5655 .12789
表6 情感性社会网络高、低两组老年人幸福感均值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幸福感均值
Equal variances assumed Equal variances not assumed
Levene’s Test for Equality of Variances F 2.768
Sig. (2-tailed) .021
T-test for Equality of Means t -1.176 -2.269 df 45.5 23.78
Sig. (2-tailed) .141 .342
Mean Difference 2.876 1.216
2.1.3社会交往网络规模对幸福感的影响
如表2所示,社会交往网络规模与老年人对生活的兴趣和计划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且与“愉快的心情”存在正相关,这说明广泛交往有利于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同时,经常参与社会交往的老人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具有较强的信心。但如何确定这种相关性的方向,即社会交往确实对老年人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不是因为参与社会交往的老人本身就是健康的老人?为此,笔者在控制老年人健康因素的情况下对“社会交往网络”和“对健康的信心”进行偏相关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依然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表7 控制健康状况因素下的社会交往与对健康的信心相关性检验
Control Variables 社会交往 对健康的信心
健康状况 社会交往 Correlation 1.000 .567
Significance (2-tailed) . .028
df 0 127
对健康的信心 Correlation .567 1.000
Significance (2-tailed) .028 .
df 127 0
2.2 异质性和同质性: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社会网络的同质性指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社会网络成员在某种属性上的相似之处,它根据考察标准的不同而变化。通过对在综合考虑生活地域、年龄、血缘、职业等各方面因素之后,最终选定了以年龄衡量同质性与否 ,在此基础上对同质性与幸福感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如表8所示,如果仅考虑单个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对生活的兴趣与计划”总变差(112.32)中由社会网络质性状况可解释的变差为96.86,由抽样误差引起的变差为16.46,其方差分别为8.038和3.141,F统计量的观测值为2.559,对应的P-=.039<.05,社会网络的质性状况对老年人生活兴趣产生了显著影响。
表8 老年人社会网络质性状况对老年人“对生活的兴趣与计划”影响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16.46 12 8.038 2.559 .026
Within Groups 96.86 41 3.141
Total 112.32 53
相同年龄意味着以相同方式、相同态度和精力参与交流。而通过与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交流,老年人可以获取新鲜消息,也会使得对话更愉悦。尽管老年人主观上并没有表现出对异质性社会网络对象的需求,异质性交往带来的积极影响却是存在的。
2.3 社会网络对老年人生活内容的均衡性调节
社会网络三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和同质性状况都会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除此之外,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纽带”,通过将个体由单调的个人生活纳入社会生活,也给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老年人生活内容的均衡性调节,即减少了老年人独处的时间,增加了其被“某些积极事项”占据的时间。
情感性、工具性和社会交往性网络及当中的各个结点 都强调“动态”和“联系”,即只有在相互联系中才能发生相互作用。据此推测,社会网络对幸福感的作用之一正是通过使老人“参与”到扩大化的社会生活中实现的。在此可提出假设:“参加活动和交谈的时间越长,老年人的幸福感均值会越高;同时,‘独处、无所事事’所占比例的越大,幸福感均值将越低”。但下面的分析结果似乎并没有完全证实该假设。
表9 控制养老方式因素下“参与时间”和“独处时间”与幸福感的相关性检验
Control Variables 幸福感
养老方式 Involved Time Correlation .667
Significance (2-tailed) . .428
Imparted Time Correlation -.719.
Significance (2-tailed) .021.
数据表明,控制“养老方式”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参加活动和交谈的时间越长,老年人的幸福感均值会越高”的假设成立,两者之间尽管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但其显著性t=.428>.05不能说明相关性的可信度。而“独处、无所事事所占比例越大,幸福感均值就越低”是成立的,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达到-.719。这说明,“参与状态(involved)”并非总能对老年人起到积极作用,过多的活动参与可能加剧老年人的忙碌感和疲劳。但是独处(imparted)状态却明显降低了老年人幸福感。社会网络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部分是通过减少独处来发挥的,独处会使老年人思考过多,陷入忧郁之中。因而,社会网络确实对老年人的生活起到了一定的均衡作用,且这种作用对幸福感具有明显影响。适当减少老年人独处并将活动量控制在恰当范围内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3 “社会网络―幸福感”路径下城市养老的不足
3.1 偏离“幸福”的目标导向与“区隔式”生活环境
老年人本身有很强的交流欲望,他们更希望在物质支持外得到真正的关心。然而不论是城市养老机构还是子女本身, 目前都存在重视物质效率而忽略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的问题。一些子女希望父母选择居家养老, 却很少为父母提供除资金以外的支持; 也有一些子女选择把老年人送进养老院, 之后很少关心、探视,而大部分养老机构更侧重于照顾老年人的衣食起居和身体健康, 并不关注老年人的内心生活状况。在这种养老导向下, 老年人社会网络以工具支持为主, 社会交往网络与情感网络相对不足, 其后果之一是导致许多老年人的生活缺乏计划性、精神生活混乱。尤其是在一些规模较小、环境条件差的养老院或交通不便利的社区, 老年人几乎处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虽然老年人生活在养老院有其他老年人相伴, 但是由于思想交流仅限于老年人之间, 使老年人更容易产生伤感、恐惧的心理和孤独感。他们的生活简单、重复, 抱着“过一天是一天”、“坐着等死”的心态生活, 精神状态萎靡。养老工作仍然停留在“老有所养”的阶段。 其次,互相区隔的生活环境缺乏建立社会网络的有效“场景”,从而为老年人社会网络的缺失设置了客观条件。城市两极化和空间重构形成了“连续、割裂、多中心的社会空间结构”[4],导致现代城市空间不断分化、社区结构松散,最终将城市老年人“逼入”区隔式生活环境当中。一方面,传统家庭结构在城市已然销声匿迹,“空巢家庭”已成定局,现代经济活动对社区公共生活空间(如广场)的入侵则逐渐将老年人“赶回”狭小而分离的住房空间;另外,生活环境的分离进一步加剧情感上的冷漠,使得社区内部的老年人很难发展起稳固而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网络关系。另一方面,尽管养老院提供了集体生活的环境,但“区隔”仍然存在。由于工作绩效并不必然激励养老院对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改善,有效集体活动十分稀缺。受身体状况和活动能力的限制,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范围也被“圈禁”在共有宿舍当中,主要就是聊天、下棋。也有个别养老院开展集体运动,但次数很少,这些活动最终不足以打破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也因而无法在老年人之间形成有效联系。
3.2 幸福感“创造”中社会网络关键元素介入不足
社会网络中的许多角色在增强老年人幸福感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现代城市生活造成了经济生活与情感生活的分离,那些社会网络中的“关键元素”正淡出老人们的日常生活。
3.2.1远离的子女与孙辈:城市生活方式下不对等的精神寄托
城市带来了多维的市民生活空间,但并未增加子女与老年人的接触机会。日益膨胀发展的城市背后正在出现一种强化的精神冷漠趋势,即便是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也不能对此有所改善,“以金代劳”似乎成为大多数成年子女面对养老问题时的第一选择。然而在养老问题上,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物质支持是必须的,但这种作用仅仅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不可能代替子女的探望、相聚所带来的心理慰藉。
情感网络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起着正向的作用,情感网络构建得越好,所获得的幸福感就越强。长期以来,子女以及延续子女生命的孙辈一直占据着老人们情感世界的中心。调查显示,有75% 的老人认为在对自己最重要的人中,孙子孙女是一个部分。如表所示,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子女与老年人的亲密关系对幸福感均值存在显著影响 。
表10 子女与老人的关系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ANOVA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501.11 49 21.038 2.265 .039
Within Groups 706.61 82 9.290
Total 1207.720 131
然而根据调查结果,目前大约63.3%的子女并没有参与到老人的情感网络构建中,老人对子女和孙辈的精神寄托胜过其子女和孙辈对他们的精神寄托。养老院中的老年人多是被子女出资寄养。子女们认为花了钱安顿了老人就算尽了孝心,加上工作繁忙,他们很少再去养老院看望。在家庭养老中,许多老人成为了被家庭遗忘的人,他们在看似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实则内心强烈渴望与子女和孙辈接触,希望回到家庭的环境中享受天伦。
3.2.2志愿者介入不足:短暂参与和参与间断
我国是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的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养老服务人员的需求与供给存在很大缺口,亟需形成一种新的既能服务周到又成本低廉的供给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志愿者服务的老年服务模式。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志愿者只是充当养老活动“临时参与者”的角色。志愿者通常是一些在职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去有需要的地方进行援助,所以对养老活动的支持通常是间断的、短暂的,缺乏连续性。此外,出于某些个人原因,一些志愿活动的进行流于形式,虽然过程相对隆重,实际带来的帮助却很少。还有一些抱着为老年人献爱心的心态去参与志愿工作,却因为不能承受条件的艰苦和工作的繁重而半途放弃。这些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志愿者在养老活动中作用的发挥,他们虽然都怀有对老年人的爱心,却不能长期、稳定地为老年人带来有效的帮助,也就不能真正走进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中心,弥补其长期存在的精神生活空白。
此外,作为社会资源的志愿者在各个养老机构之间的分配上存在“供求不均衡”的问题。大型公立养老机构由于知名度高、社会关注度高,更容易吸引志愿者的参与,往往出现志愿者过剩的现象;而小型、私立、交通区位较差的养老机构对志愿者的需求量很大,却很少有志愿者关注。由于各养老机构相互独立,很少自发开展交流合作,这种由“身份”带来的资源差距逐渐增大,形成城市养老机构在争取志愿者资源方面的“马太效应”。
3.2.3老年社团组织:尚待挖掘的社会资源
社团成员身份是社会网络发展的重要形式,也是开展并维系稳定社会交往的基础。加入老年社团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类似于家庭的生活环境,进而全方位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各因子水平。然而,老年社团在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方面似乎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老年社团主要存在于经济、文化条件原本就较好的社区和养老机构中,而条件较差的养老院和社区并不能与老年人社会团体建立联系,这就使得老年社团的作用难以从其他替代性变量的作用中准确剥离出来。
换言之,社团组织确实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幸福感,但是其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据统计,25.4%的老年人在自己的交往网络中提到了社团组织,有鉴于此,需要在养老院和城市社区发展老年社团,比如秧歌队、太极拳健身队、集体观看电影等等,以此为老年人幸福生活提供依托。
表11 控制社会网络规模下社会团体对老年人幸福感各因子的相关性检验
Control Variables 幸福感 精力 控制 健康 兴趣 愉快 接纳
社会网络规模 社会团体 Correlation 567 .231 .643 .227 .598 .611 641 Significance (2-tailed) .428 .311 .397 .345 .196 .267 .246
3.3 老年人社会网络获致能力分化与“孤立节点”的出现
社会网络是社会关系以人为中心的扩展和交织物,其基础是单个社会关系的形成,有“先天”与“后致”两类因素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建立。一是社会地位。这是一种先天因素,退休前的老年人处于何种地位,很可能对其社会网络的成分和规模产生影响。二是先天性格因素。性格孤僻的老年人一般不愿意与人交谈,产生自我封闭倾向,从而限制了社会网络的扩展。热情、开放的老年人则更愿意全力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三是外在环境构建。生活环境(包括生活气息,社区氛围,地理位置,公共设施)因素影响着社会网络的发展。处在活跃的“场”中,老年人更容易获得与这种“场”相符合的社会网络。四是外在政策构建。这主要包括养老机构、社区和政府所采取的与老年人有关的措施、行动和方案等。
社会交往可以促进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如果老年人能够以乐观的心态与他人交往,建立稳定的交际圈子,那么他们在遇到困难时也会更及时地得到帮助。所以老年人幸福感的背后还是一种寻求能力。调查发现,有部分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明显小于他人,其幸福感水平也低于相同年龄的其他老人。这些老人大都是家庭背景特别差,部分老年人性格孤僻,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年龄较高、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这部分老年人只能入住条件较差的养老机构或者被动接受封闭的家庭养老。他们很少参与社会活动,也很难与其他人建立亲密关系,难以得到来自外界的物质、体力支持和精神慰藉,从而造成恶性循环。这部分老人成为幸福感追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游离于现有社会网络系统之外,难以融入周围的生活,更无法获得来自他人的情感、物质与交往支持。
4 “社会网络―幸福”指向的幸福感提升策略
4.1 社会网络与老年人幸福生活内涵变迁
青岛市老年人幸福感六个因子均值为3.7034, 大于理论中值, 说明老年人普遍感觉较为幸福。在幸福感的6个自评维度中,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得分最高,精力得分最低, 对生活的兴趣与计划得分也较低, 且对健康的自信具有最大的标准差。这说明老年人总体上能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但普遍表现出精力和生活兴趣的缺失, 尚未进入“老有所乐”的阶段。
表12 老年人幸福感基本情况
N 均分(M) 标准差(SD) 排序
愉快的心情 1050 3.5845 0.55 2
对生活的兴趣与计划 1050 3.4677 0.33 5
对健康的自信 1050 3.7543 4.76 3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1050 3.8977 0.64 1
精力 1050 3.3141 1.88 6
自我接纳与评价 1050 3.6476 2.14 4
幸福感总体 1050 3.7034 0.71 ------
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其水平受到但不完全受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它是排除了恶性情绪的心理状态。“幸福”的晚年生活应当包括良好的社会性因素,即“充满人文色彩”的生活,“人文”养老和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愉悦已经成为幸福晚年的核心指标。老年人生活的重心已经不是获得报酬、争取社会地位,而是“幸福地安度晚年”。
现实生活中的老年人往往在退休后淡出公共视线,其社会交往圈也因“场合”的减少和身体素质的下降而逐渐缩小。因此养老工作不应继续将目标局限在为老年人提供生存场所和物质保障上,而是要扩大视野,帮助老年人在晚年寻求进一步发展,以改变老年世界的“灰色形象”及其在社会交往中的边缘化命运。养老机构与各社区应充分认识扩展老年人和“准老年人”社会网络的意义所在,充分认识“老有所为”和“社会参与”对他们的积极意义,而不应该只把老年人看成领取退休金的社会负担或者一味将其当做弱势群体而小心地从社会中剥离出去。“老有所为”、重新融入公共生活恰恰是许多老年人最高的精神需求。
因此,应当改变传统的“养老文化”,通过完善其必要的社会网络结构使老年人重新成为“社会人”并为其重新参与公共活动提供方便,最终促进老年人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自身价值、增强老年自我认同、提升老年人幸福感。
4.2 基于社区的社会网络重建:培育“公共空间”,减少老年独处
提高老年人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构老年人社会网络,减少其独处时间。从家庭结构和亲属关怀入手可能是容易想到的思路,为此有关部门可促成设立“老人寿辰专门假”, 鼓励中年工作人员与年轻人回家看望老年人, 增加每月与老年人的交流次数,形成“祖、父、孙”三位一体的家庭社会网络[5]。但正如表11所示,维系老年人情感世界的“任务”正在转而由室友或邻居来完成。也就是说, 社区老年人正由传统的“家庭”进入一个更大的公共空间, 在此空间内正孕育着改善老年人生活的新生力量, 同时这些新生力量并未足够强大, 仍然存在很大的挖掘培育潜力。
公共空间通俗地讲就是社会成员集体生活、共同拥有的场合,是形成社会资本、完成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这种“松弛和自由的空气,及此种公共游艺需要众多的参加者各点,都可促成新的社会结合”[6]。当然,公共空间也不会自发出现。尤其是在空间区隔和精神淡漠的现代城市社区,培育公共空间需要提供老年人集体活动的场所和事件。
对养老机构来说,应考虑绩效评估中加入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测评指标,抑制养老院工作的“硬指标”趋向。工作人员应积极加入老年人情感网络,保证老年人的情感网络的存在,尤其是对行动不便、年龄较大的老年人,要保证其“陪伴率”,降低独处带来的精神焦虑。养老院内部应保证规模较大的集体活动,并力求扩大成员参与度,以此增强老年人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异质性,引导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和健全的娱乐设施。 对社区来说,首先成立从居民楼到社区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合理组织和开展各种文化及体育活动,进行老年保健的宣传与教育”[7],使社区老年人有充足的时间和场所进行共同交流,打破建筑区隔下的冷漠生活氛围,充分挖掘认识社会网络成员在“相互联结”与互动中形成的双向关系,以信任文化促进邻里之间的深度交流。其次,登记同一楼层、同一单元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在此基础上按照空间接近的原则建立老年人家庭联合扶助小组,由社区自治组织牵头建立家庭之间的深度信任与合作,形成扩大化的“类家庭”,不同家庭中的老年人互相照料、互相提供物质和情感交流支持。第三,组织成立社区老年人协会,通过吸纳老年人进入社区志愿管理、卫生清洁、幼儿园协助管理与生活教育等领域,使居家老年人重返公共生活,实现自身幸福感。
另外,重视社会团体在老年人生活中的作用。社区、养老机构可以筹划建立或者引进老年社团,如老年象棋团、老年舞蹈团,丰富老人生活,保证尽量减少老年人除必要生活环节之外的独处时间,并通过社团成员的深度交往弥补家庭结构变迁带来的负面影响。
4.3 “孤立节点卷入”与应急心理干预:主动介入的养老策略
表13 老年人配偶状况对幸福感各因子均值影响的t检验(部分)
与配偶 感情好 感情不好 多年无配偶 新近丧偶
样本数 435 105 360 150
幸福感均值 3.9623 3.2562 3.6723 3.0122
t值 .897
Sig(双侧) .032
生活兴趣均值 3.9332 2.96222 3.7323 2.7212
t值 .232
Sig(双侧) .011
健康信心均值 3.7237 3.7638 3.9638 1.2621
t值 1.21
Sig(双侧) .048
愉快轻松均值 4.9032 3.2123 3.9828 3.2023
t值 2.67
Sig(双侧) .039
自我控制均值 3.9020 3.1638 4.3781 3.0603
t值 .992
Sig(双侧) .021
面对“区隔式”的生活环境,社区内部各成员缺乏沟通接触的机会。加上缺乏外部力量的有力“挤压”,整个社会网络系统呈现出结构松散的特征。由于经济条件、性格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不断有新的网络节点从系统中脱离。为此,可通过两种方式为处于“孤立节点”处的老年人提供支持:一是充分动员养老机构与社区成员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保证贫困老年人基本的日常支出,通过减轻生活负担消除其自我封闭、自卑,提高“对生活的兴趣和计划”和“自我评价与接纳”水平。二是采取必要的社会交往干预,以社区工作者上门服务、发放电影券来补充传统的救助金发放,并要求受助者参与一定的公益、公共活动,以“卷入”的方式将“孤立节点”纳入现有的社会网络体系。对于因年龄与健康条件限制而不便行动的老年人来说,则应在尊重家人意愿的基础上,尽量通过保证一对一社工照料提高其幸福感水平。
此外,老年人的“孤立”状态还具有心理上的含义。受异常生活事件的打击,老年人极有可能从心理上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在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中,配偶是一个重要因素,能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的支持。多数城市老年人在寻找生活照料和倾诉心事的支持中更倾向于自己的配偶[8],如果遇到丧偶等其他事件的冲击,很可能造成其心理失衡。如下表所示,新近丧偶的老年人不论是在幸福感总体水平还是在各个因子上都明显偏低 ,而据此类推,新近患病或者家庭情况出现变故的老年人也将经受心理上的极大痛苦。城市老年工作缺乏针对重大生活变故的事件统计心理调适内容,而“通过健康宣教和聊天的方法向老年人介绍心理、生理特点及常见的健康问题”[9],有利于缓解老年人自身的心理压力。因此,应当建立完善的老年人心理调适志愿工作者制度,对丧偶老人及时进行心理调适的干预,帮助其恢复正常生活状态。
4.4 志愿者工作和跨社区合作:增强社会网络异质性与可延展性
不论是机构养老还是居家养老,老年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都因其活动能力的减弱而表现出严重的固化倾向,既不能使已有的社会网络更加紧密、成员之间联系更加密切,又不能实现网络成分的更新以提升异质性。这种固化倾向不利于老年人从周围环境中随时获得生活兴趣与外来资源。根据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充当信息桥”[10]的理论,信息桥作为连接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社会网络系统的中介,能够促进不同区域社会资源的交换与流动。应增强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可延展性,建立老年人社会网络的“信息桥”以承接外部养老资源,促进老年人社会网络向外部扩展。首先,可以通过加大宣传或政策支持的方式,鼓励社会工作人员走进老年人生活,尤其是鼓励志愿者面向小型、私立养老机构和偏远社区开展志愿工作,切实改变城市老年人“志愿真空”状态。其次,不同养老机构、不同社区之间也可以建立联系,相互学习养老工作经验并定期开展联合交流活动,甚至通过开展交换养老机构、生活社区项目实现老年人幸福感水平新的提升。
总而言之,应重视社会网络在老年人幸福感培育中的重要作用。三种社会网络在老年人生活中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应当有策略地发展:重视情感性网络的深度和存在性;对居家老年人来说,要重视工具性网络在物力支持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对养老院老年人而言,则要保障其资金支持的充足性。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频度要适宜,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未来城市养老工作需要实现质的转变,重塑老年人社会网络则是当中不可缺少的一步。
注释:
1 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心理学动态》1996年第1期)从个性特点、自尊心、控制源倾向、自我概念、心理成熟度等主观因素和社会关系、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各种生活事件等客观因素方面分析了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梁渊等(《农村高龄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国老年学杂志》,2004年第2期)则认为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经济状况、长寿、担心无人供养、担心子女不孝顺以及希望菩萨保佑等。薛兴邦(《社区老人幸福度及其相关因素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年第1期)等调查结果显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涉及与子女关系、与配偶关系、团体活动参与程度及住房满意度。 2 (1)公共服务决定论:养老的主体是国家政策与政府行为,养老问题出现的原因归结起来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政府公共投入太少,农村养老机构建设欠缺,如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12期)关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研究。(2)生理机能决定论:以心理学和医药学为理论指导,认为老年人心理状况和生理健康状况将决定养老生活的质量。比如王洁(《体育运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年第5期)认为增加老年人体育活动是提高社区老年人幸福度水平的重要策略。(3)社会结构决定论: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出发,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使家庭结构和子女养老观念发生变化,传统家庭养老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如梅锦荣(《老人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性因素》,《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年第2期)指出,老年人生活满足感以及抑郁症状则与社会网络,尤其是家庭网络和互依关系有更显著的相关。
3 由于老年人社会网络成员数量较小,故此处只考虑“有”和“无”的问题,不考虑成员年龄段的分布。
4 检验的F统计量的观察值为2.768,对应的概率P值为.021。如果显著性水平??=.05>p,则可以认为两总体的方差具有显著差异。其次,由于两总体方差具有显著差异,所以应看第三列(Equal variances not assumed)的t检验结果。其中t=-2,269,对应的双尾概率P值为.342>.05,因此没有足够证据断定两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尽管老年人情感性社会网络的规模不同,但仍未给幸福感造成显著差异。
5 为方便研究,笔者在数据中生成新变量,0-3分记为“同质”,4-7分为“异质”。
6 在社会网络相关理论中,用“结点”来代指各个成员。由于每个人所熟知的人相互交叉,孤故而形成网状,而整个网络又是靠每个人来连接起来的,所以称为结点。
7 如果仅考虑单个因素的影响,则老年人幸福感总变差(1207.720)中与子女不同关系的影响可解释的变差为706.61,抽样误差引起的变差为501.11,它们的方差分别为21.038和9.290,相除所得的F统计量的观测值为2.265,对应的P-值为.039<.05,所以与非独生子女的不同(亲密)关系对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
8 当中均值的方差t=0.897,p=0.032<0.05,说明不同配偶状态下的老年人幸福感确实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生活的兴趣与计划、对健康的信心和自我控制三个因子中,α值均小于0.05,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