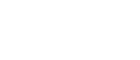摘 要:3H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同时进入到法国,这使得法国哲学界呈现出一道匪夷所思的景观:黑格尔是经过依波利特诠释过的黑格尔;胡塞尔是经过萨特、芬克和唐·迪克陶折射过的胡塞尔;海德格尔是经过萨特曲解过和勒维纳斯警醒过的海德格尔。这一切给德里达早年的学术视野和理路提供了基本的运思框架:“思辨性差异”、“有限性”、“存在的辩证法”、“原素”、“延迟”、“超世间性”、“拆解”和“绝对的他者”等等。再现这一历史文本的效应过程不但能廓清德里达早期思想研究上的迷雾,同时也能防止国内有些学者单纯从文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德里达思想作望文生义的解释。
关键词:德里达; 黑格尔; 胡塞尔; 海德格尔
晚近的法国哲学主要是对3H(即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主旨思想及其所提出的问题的阐明和深化,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1](P9)。但是我发现,与这一事实同时呈现的是一道令人称奇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景观。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德国思想史上虽分属不同的历史时期,且他们的问思方式和理论根基截然不同,但他们却在一个狭窄的历史时段几乎同时挤入到法国学术界,这从下面几个事件的时间表上就可以看出来:1939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一卷由J. 依波利特(J. Hyppolite)译成法文出版,1941年,《精神现象学》第二卷问世;但是,一方面,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早在1931年就已经与海德格尔的《论根据的本质》同期在法国面世,而另一方面,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直到1963年才有了完整的法文版;当依波利特等最优秀的黑格尔主义者在三十年代登上学术舞台时,1930年的G. 古尔维茨(《德国哲学目前的倾向》)和勒维纳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的现象学研究已经颇见功力,至于法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从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直接的对抗”[2](P658)就已可见一斑。短促的时间、狭窄的空间,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多元而交错的对话,这一切使3H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产生了匪夷所思的效应: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在遭到扭曲和误解之后才进入到法国人的视野。例如,从20年代起,法国学术界就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并无本质不同,他们想通过贬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方面向人们呈现出一位胡塞尔化了的黑格尔,而且甚至想向人们呈现出一位黑格尔化了的胡塞尔,依波利特直到六十年代还在尝试对这两种现象学之间的相近之点进行揭示,施皮格伯格对此“惊奇”不已:
“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德国现象学的人来说,法国现象学令人感到惊奇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毫不犹豫地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理所当然地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近,甚至是从那里起源的。不管这种联系是否能够证实。”[2](P609)
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进入到法国时也在萨特、梅洛-庞蒂和勒维纳斯等人那里进行了过滤,特别是萨特,他对德国思想的扭曲差不多与他对法国学术的贡献一样巨大,他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误解使得后一代法国学者几乎不得不从头开始,90年代以后德里达在回忆往事时对此仍深有感触:
“我们已开始以另一种更为严格的方式去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与萨特分道扬镳了。”[3](P28)
德里达正是成长于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时期,这使得他的哲思的支援背景显得盘根错节且极为费解。我的理解是,德里达在进入胡塞尔文本之前以及在现象学研究的过程当中,他在理论上的支援架构并非是原教旨意义上的3H学说而是经过法国思想家(也包括德国学者)扭曲、误置、过滤和折射了的思想,共有三条隐性的支援背景支配着德里达的运思。
背景一:经过依波利特(还有德鲁兹)诠释的黑格尔
在德里达的第一部作品(虽然直到1990年才出版)《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以下简称《生成》)中通篇见到的是对“辩证法”毫无顾忌的使用[1],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与黑格尔的关系。不过,这里的黑格尔已经是经过依波利特所中介过的黑格尔了。依波利特对德里达的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德里达“延异”(différance)原理的第一要素“差异”(difference)概念最早见之于依波利特的“思辨性差异”(speculative difference)。依波利特通过黑格尔的差异和矛盾思想竭力构想发生在逻辑生成之中的差异之本质,他认为,经验意义上的量的差异意味着一物只有在它的他物中才能发现自己的存在,矛盾内在于存在自身之中。[4](P187)
第二,有限性的不可或缺问题、完全恢复意义的不可能性以及直观主体存在的多余性。前者是德里达在《生成》中借以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以及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别开来的主要指征,中者是德里达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译文与导论》(以下简称《几何学的起源》)中与胡塞尔进行抗争的立足点,而后者则是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解放含义之束缚的有力武器。这三点我们都可以在依波利特下面的一席话中找到:
“谁或什么在说话?答案既不是‘某人’(或者说,das man)也不是‘它’(或‘the id’),更不是‘这个我’或‘我们’。‘辩证法’这个名字是黑格尔所复活并加以阐释的,它标志着事物自身的辩证法,它不是知识的工具,它自身就处于这一问题的核心之中……对黑格尔来说,这不是一个否定神学的问题,也不是所谓的超越意义之外的意义问题,而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有限性问题、一个意义之丧失(就像我们谈到事业失败一样)的问题,这一失去的意义绝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恢复。”[2]
第三,德里达使用了依波利特在阅读黑格尔中所开发的术语,如“向有限的过渡”,“绝对者是过程”等等。此外,依波利特所理解的本质与现象的相互开放、相互转化实际上就是德里达在《生成》中所说的观念与事实、先验与经验的相互污染。[4](P186)
第四,G.德鲁兹对德里达的差异概念也给与了极大的启发。德鲁兹在1954年给依波利特的《逻辑与存在》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法国与外国哲学评论》 (1954)上,他说,“在所有这些当中有一点是,依波利特同时表明了自己的黑格尔性:只要差异被提升为绝对之物,就是说,提升到矛盾,那么存在就能够与差异相同一。思辨的差异就是自我矛盾着的存在……以[《逻辑与存在》]为基础,我们可以这样问:难道我们不能构造一种差异的本体论吗?——这一本体论不必上升到矛盾,因为矛盾低于差异,或者说不会高于差异。难道矛盾本身不就仅仅是差异的现象的以及人类学的方面吗?”[4](P188)
我们知道,德鲁兹与德里达同为依波利特的学生,而且德鲁兹在196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差异与重复》。从上面所引的这段话来看,依波利特及其两位高足早在5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探讨差异(difference)问题,而且他们的研究理路非常独特,如差异的绝对性、差异与存在的同一、差异不同于且高于矛盾等等,这些都是德里达后来一直坚持的解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德鲁兹把差异本体化的倾向直接为德里达在《生成》中所吸收。
依波利特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德里达对此也是乐于承认的。德里达在《几何学的起源》的一个脚注中明确说道,依波利特的《逻辑与存在》是“一个在诸多方面对黑格尔和胡塞尔思想进行深层聚合(convergence)的著作”[3]。
背景二:经过萨特、芬克和唐·迪克陶折射过的胡塞尔
这三位人物都是德里达学术上的前辈,他们对德里达心目中的胡塞尔形象的塑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德里达正是通过他们才知道了现象学的独特工作方式、与众不同的研究领域以及它的尚需弥补的缺陷。
把萨特排在第一位,也许有点出人意料,德里达在其早期的现象学研究中几乎没有提到过萨特,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德里达这一时期的很多观点的确与萨特非常相近,特别是在他的第一部作品《生成》中,他为现象学的改造所提供的思路简直与萨特如出一辙。
H. 施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中谈到萨特对胡塞尔所作的“意义深远的批评”对我们这里的论证极为有利。施皮格伯格罗列了一大堆萨特对胡塞尔的“指责”[2](P656-657):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指责胡塞尔“不忠实”于他原来的现象学观点;指责他陷入“纯粹的内在论”;指责他未能避免“事物幻觉”(通过对意识图像引进一种被动的原素[hyle]和感觉说来获得);指责他“仍然胆小地”停留在“功能描写”的层次上,这种描写使他局限于对现象本身做出叙述,从而不能进一步探讨“存在的辩证法”;指责他“尽管自己做过否认,仍然是个现象主义者而不是现象学家”;指责他仅仅给我们一张关于真正超越的漫画,后者应该超越意识进入世界并且超越即时现在而进入过去和未来;指责他和康德同样未能避免唯我论,特别是由于引进“先验主体这个无用而又致命的假设”;指责他没有充分论述我们的直接经验的执拗性。萨特在《自我意识与自我认识》的论文中还指责胡塞尔从来没有提出过本体论的问题,这使得关于世界的存在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也使得我们从来没有从现象学还原回到世界上来。
让我们再来比照一下早期的德里达。德里达在《生成》中抓住了胡塞尔的“原素”(hyle)这一概念大做文章,指出现象学在这一点上的漏洞和困难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为现象学奠定本体论的基础;他还认为,他人的存在的不可还原性说明胡塞尔无法走出唯我论;他也认为胡塞尔本质上是个现象主义者而非现象学家;直到《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仍然在寻找胡塞尔对自己的“不忠实”即自相矛盾之处(尽管严格的文本学将会证明很多时候这是他对胡塞尔的误读)。
另外,根据C. Howells的考证[5](P33),萨特对“自为”的“自身在场”的分析要比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的分析早二十多年。《存在与虚无》第二部分第一章引用胡塞尔为例说明即使是最坚决的在场哲学家也不能完全回避隐含在一切意识中的反思性。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还像后来的德里达一样讨论了时间的本质,甚至在此基础上提到了“延迟”的思想:“自为”事实上总是含糊不定的,因为它的存在是不断的延迟和延期[4]。
很明显,尽管德里达“已开始以另一种更严格的方式去阅读胡塞尔”,尽管德里达已经“与萨特分道扬镳”,但萨特的观点和话语却始终是德里达无法摆脱的阴影。C. Howells也表示了相同的惊讶:“在胡塞尔的个案中,德里达自己的分析同萨特的惊人地接近,而且他的现象学批判的基础几乎与萨特是同一的。”[5](P33)
德里达为什么要掩饰他与萨特之间的传承和亲缘关系呢?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C. Howells对此作过一些提示,也许可资参考:“20世纪60年代德里达对萨特的态度是叛逆的。当德里达似乎在重复他不愿承认其构成先驱者文本的一种分析的一般思路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30年之后,当他带着明显的愉快去探讨他们政治和哲学某些方面的共同立场时,德里达对他的态度明显宽容了。”[5](P33)
芬克(Eugen Fink)是德里达在早期的胡塞尔研究中常常引用的人物,德里达并不讳言芬克对他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芬克1933年的突破性作品——“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与当代思想”——给他带来的剧烈震撼。德里达在《生成》的写作过程中就已接触到芬克的这个文本并把它列入该书的文献目录。芬克的这篇文章(据说曾得到过胡塞尔的首肯)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胡塞尔晚年的亲密助手和胡塞尔思想的最权威的解释者,他在文中讨论了先验现象学的几个悖论。芬克认为,先验之我与经验之我不同,但不是不同的“某物”,它的存在与心理学自我的存在相互重叠。他们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世界上已发现的任何事物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逻辑能对此加以解释。它的本质是现象学最根本的悖论。这些悖论都起源于这一事实,即先验现象学试图为世界的存在提供一个“超世间的”(extramundane)的基础——同时无须把这一“超世间性”(extramundaneity)设定为纯粹的超越性。这一基础必须同时是内在的和超越的。在芬克看来,为了在基础这一问题上与他人交流,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使用世间的(mundane)语言,而这需要一个新的差异逻辑。[6](P144)
芬克对先验现象学悖论的揭示引起了德里达极大的兴趣,他在“‘生成和结构’与现象学”(1959年)一文中详尽地描述了观念对象的先验性存在方式,在一篇关于“现象学的心理学:胡塞尔1925年夏季学期的讲座”[5](1963年)中德里达花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介绍了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之间的平行关系的特殊性,这一介绍后来在讨论先验之我与经验之我的“令人震惊、奇妙非常的”(德里达语)“平行论”时又原封不动地直接搬到《声音与现象》中。
提到唐·迪克陶[6],“德里达先生……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和他的许多从现象学开始哲学生涯的同代人都受到过迪克陶的《现象学和辩证唯物主义》这部著作的影响”。[7](P27)《现象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主旨思想是一方面把辩证法引入到现象学之中,另一方面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通过对动物心理学和经济历史的分析,提出一种有关意识起源和理性生成的理论,也就是说,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为现象学寻找本体论的基础。从德里达早期著作对唐·迪克陶的引用和批判来看,唐·迪克陶至少有三个观点得到德里达的注意和认同:第一,当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把几何学的真理奠基于人类实践(Praxis)之中时,他已经朦胧地预感到回到外在的、现实的存在和经验的、事实的历史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并不意味着回到经验论历史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我们所处的层面位于还原之后,但这种还原并没有删除现实的自然(wirkliche Natur),现实的自然在其发展中蕴涵了主体性的全部运动;第三,这种主体性运动决不是主观主义,相反,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正是他的“主观主义立场”阻止了他的哲学的进一步跨越[7]。特别是唐·迪克陶的第二个观点值得关注,它能使我们避免这样一种常见的误解:辩证法以及后来的解构主义彻底铲除了胡塞尔的主体性思想。德里达从未抛弃主体性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改造的“先验主体性”概念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背景三:经萨特曲解过和经勒维纳斯警醒过的海德格尔
萨特对海德格尔的严重误解,这已是包括德里达在内的法国第二代现象学研究者的集体共识,正如德里达所言,当他意识到萨特对海德格尔解释的欠缺和随意性之后,他便与萨特分道扬镳,从而开始以另一种更为严格的方式去阅读海德格尔,这个时期大约是在六十年代早期。
尽管海德格尔对德里达的影响也像黑格尔和胡塞尔的影响那样经过了中介,但比较而言,他对德里达的作用较为直截了当,——特别是当德里达注意到这种曲解之后。这可从他们对某些概念和方法的共同使用上看出。第一,有些概念的提法虽然不一样,但究其内容而言却具有一致性的方面,例如,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提出了“对本体论的历史进行摧毁(Destruktion)的任务”,“摧毁”其实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拆解”(Abbau),也就是德里达所谓的解构(la dé-construction)的前身。第二,有些概念的使用不只是相近,甚至在含义和论证方式上也完全一致,例如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就是这样。海德格尔声称,“在场的形而上学”把存在等同于在场,但这样做恰恰忽略了某物作为某物的在场正是由非在场作为前提的,正是非在场才使在场成为可能。“摧毁”或“拆解”所追寻的就是这一非在场的经验。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理解与海德格尔并无不同,不仅如此,他还直接把海德格尔在这里的论证方式巧妙地应用在对胡塞尔的代现理论的批判之中,他模仿海德格尔的口吻说,正是非呈现才使呈现得以可能,从根本上讲,呈现就是再现,它并不奠基于自身而是奠基于非呈现、非在场即缺席和过去之中。
第三,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思想对德里达深入思考“差异”问题并最终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的“差异”思想区别开来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Leonard Lawlor对此的考证令人颇为信服:
“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思想涉及两个相互交织的对德里达的挑战,德里达正是在这一时期作出回答的。一方面,‘本体论差异’激发德里达思考基础(the ground)即存在(Being)问题,基础(the ground)决不依赖于被奠基者(the grounded)即诸存在者(beings)。换言之,基础决不是某种类似于它所奠基的东西,否则基础就预设了它所奠基的东西,这样它就根本不是基础了。另一方面,本体论差异激发德里达以这样一种方式思考基础(即存在),即这种方式不会导致物化(reification)。我们决不能把基础设定为一种对存在者(beings)的‘超出’(beyond),因为这会隐含结构与生成的分离,简而言之即柏拉图主义。存在永远被掩盖(dissimulated)在存在者之中。”[8](P207-208)
我们几乎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海德格尔对德里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巨大而直接的。事实上,德里达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没有海德格尔的提问所打开的东西……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对存在与存在者之间以及存在状态与存在者状态之间的差异(在某种方式上这一差异始终未能受到哲学的思考)所提起的关注,我所尝试的一切都将是不可能的。”[9](P18)
然而,事情远非这样简单。当德里达在六十年代开始广泛而深入地研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主要是晚期著作)时,意外发生了!他受到了“勒维纳斯思想的震撼”(德里达语)!这种震撼源自一种彻底的颠覆,它不是勒维纳斯的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反批,也不是黑格尔幽灵在法国思想界的重现,它是希伯来思想对希腊思想的反动和抗议,与这种彻底的颠覆相比,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乃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充其量只是希腊思想内部的一场对话而已。下面这一段勒维纳斯的话显然触动了德里达,他在1964年的论文“暴力与形而上学:论E. 勒维纳斯的思想”中引用了这段话并作了自己的引申:
“《存在与时间》可能只支撑了一个论题:即存在是不能与对(作为时间展开的)存在的含括分开的,存在已经就是对主体性的呼唤。海德格尔式的存有论至上并不依赖显见之理:‘要认识在者,就得已经理解那种在者之存在。’肯定存在对于在者的优先性就已经对哲学的本质做了表态,就是将与某人这种在者的关系(伦理关系)服从于某种与在者之存在的关系,而这种无人称的在者的存在使得对在者的把握和统治成为可能(即服从于一种认知关系),就是使公正服从于自由……一种在大写的他者核心处保持大写的同一的方式。”[10](P164-165)
德里达在写完这段话之后立即作了引申:与存在者根本不同的存在其实是“一种作为无名的非人的普遍性之状态的暴君”,“海德格尔式的那些‘可能性’仍是些权力。尽管它们要成为前技术的、前客体性的,它们却并不缺少压制性和占有性。”
比较这里的引用和引申,我们就不难理解,德里达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论文字学》中在对海德格尔进行挪用的同时也对他表示了不满:“‘存在的声音’……清楚地表明了海德格尔在对待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方面的模糊立场。”[11](P29)
除此而外,勒维纳斯的“绝对的他者”代表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对本体论进行思考的努力。“绝对的他者”显然对德里达放弃使用“存在”和“本体论”这些词有很大的影响[8]。
3H思想或以扭曲折射的方式或以警醒划界的方式作用于青年时代的德里达,他们的影响构成了决定德里达后来思想发展的核心作用圈,但德里达接受影响的范围远远不止于此。在“德里达谈现象学”中,德里达明确承认梅洛-庞蒂对他的“巨大、关键而决定性的影响”,根据国内学者杜小真女士的考证,德里达的“原印迹”非常接近于梅洛-庞蒂的“原始的过去”:“原始的延迟,原始的印迹使我们又看到了梅洛-庞蒂的‘原始的过去’”[12](P102);德里达与索绪尔在解释学意义上的相互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索绪尔的“差异”思想总是让人揣测它对德里达的“延异”观可能具有的贡献,而德里达对索绪尔的解读也让索绪尔的追随者愤而抗议,他们指责德里达给世人提供了一个经他乔装打扮的索绪尔。David Wood为我们总结了德里达与索绪尔之间的三点关系:
“第一,德里达广义上同意语言对语言使用者所具有的优先性;第二,德里达认为,索绪尔对符号(sign)的解释与他赋予言语(speech)对书写(writing)所具有的特权不一致;第三,他挪用了索绪尔的符号的区分性(diacritical)理论,这一观点认为,语言(language)只是一个差异的系统。”[13](P272)
我觉得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上第四层关系,索绪尔的“音位学原理”以及作为能指的“音响形象”的“一般原则”对德里达提出“声音中心论”及其相关批判显然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如果说3H及其解释者们(或曲解者们)算作影响德里达的核心作用圈的话,那么梅洛-庞蒂和索绪尔就是次生作用圈,属于这一作用圈的还有康德(先天综合、直观与意向、无限观念)和卢梭(书写和情感的替代性)等等。
德里达早年的学术涉猎极为广泛,这为他后来广阔的学术视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给德里达的诠释者和批评者们留下了一桩桩的悬案,谁对德里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黑格尔、海德格尔还是胡塞尔?抑或依波利特、萨特、勒维纳斯、芬克?德里达对3H以及其他学者的思想的叙述和解构是否剔除了其中遗留的扭曲、误置、过滤和折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参考文献:
[1] John Protevi. Time and Exteriority: Aristotle, Heidegger, Derrida[M].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4.
[2]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现象学运动[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 德里达.“德里达谈现象学”[J]. 哲学译丛,2001, (3). 原文收于Sur Parole: Instantanés philosophiques[M], Paris: Editions de l’aube, 1999.
[4] Leonard Lawlor. Distorting Phenomenology: Derrida’s Interpretation of Husserl [A]. Philosophy Today[J]. Summer 1998.
[5] 豪威尔斯.德里达[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6] Eugen Fink. The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E. Husserl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A]. The Phenomenology of Husserl[M], ed. By R.O. Elveto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7]杜小真. 在记忆和遗忘的下面,是生活[J]. 万象,2001,(3).
[8] Leonard Lawlor. The Epoche as the Derridean Absolute: Final Comments on the Evans-Kates-Lawlor Debate[A]. Philosophy Today[J]. Summer 1998.
[9] 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M].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
[10] 雅克·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11] 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2] 杜小真.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
[13] David Woo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ime[M].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Atlantic Highland, NJ, 1989.
--------------------------------------------------------------------------------
[1] 在1990年该书问世时,德里达在“告读者”中用“起源的污染”这一表述代替“辩证法”。在随后的两本现象学研究著作中,德里达对“辩证法”一词的使用逐渐减少。
[2] Jean Hyppolite: “ Structure du langage philosophique d’après la Préfac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 de Hegel”,转引自:John Llewelyn: Derrida on the Threshold of Sens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6, p4.
[3] Jacques Derrida: Husserls Weg in die Geschichte am Leitfaden der Geometrie, von Ruediger Hentschel und Andreas Knop, Wilhelm Fink Verlag, 1987,p90. 这一点最先是由Leonard Lawlor注意到的。参见:Leonard Lawlor: “Distorting Phenomenology: Derrida’s Interpretation of Husserl”, Philosophy Today, Summer 1998, p186.
[4] 参见:Jean-Paul Sartre: L’ětre et le nèant——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éditions Gallimard, 1981, p771
[5] 参见:J. Derrida, <>, par Edmund Husser,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18(1963).
[6] 唐·迪克陶(Tran Duc Thao)(1917-1993),越南裔法国哲学家,五十年代法国现象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是《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唐·迪克陶: Phénoménologie et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Paris, 1951)。
[7] 德里达专门用了一条长注叙述了唐·迪克陶的前两个观点。参见:Jacques Derrida: Husserls Weg in die Geschichte am Leitfaden der Geometrie, p61;关于第三个观点,参见该书,p86。
[8] 无独有偶,与勒维纳斯这种海德格尔批判的彻底性旗鼓相当的还有阿多诺,参见《否定的辩证法》第一部分(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或可参见国内学者张一兵先生对这一部分的精彩演绎(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北京,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