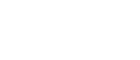20世纪最后十年里,后现代主义一再被用来描述某种思想范式、时尚风格或学术方法。被约集于这一名称之下的现象斑驳陆离,对其名称本身的溯源与界定也是五花八门。这引起了笔者对这一课题的兴趣,随即着手对其中的代表人物,法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9-)进行个案研究,以获得一些管窥之见,也算是研究后现代主义这个庞杂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利奥塔于1979年发表题为《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并在该书最后部分回答了什么是后现代艺术这个问题。由于该书的影响,他被视为后现代哲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利奥塔对后现代主义的阐述与众不同。他从考察当代知识形态入手,指出存在着遵循不同原则的各种知识类型(如科学、艺术、道德),强调不同知识之间的异质性,强调各种知识原则之间不可通约,由此否定将全部知识统合于某一共同原则之下的做法。他认为,德国思辨哲学便是将知识全部统合在绝对精神之下。例如,黑格尔将人类的全部知识都置于绝对精神的运行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扬弃,绝对精神不断向上攀升,各门知识的价值由它们在绝对精神发展进程中的位置所决定。科学知识受自身之外的原则支配,或者说从自身之外的话语(哲学话语)中获得自身的合理性,这样的理论体系就是利奥塔所说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利奥塔认为,还有一种元叙事体系是法国的启蒙主义。法国启蒙主义主张科学知识应与政治理想联盟,只不过它依靠的不是绝对精神,而是寄希望于受良好教育的国民来实现知识与理想的统一,因此特别强调对国民的启蒙与教育。
那么,所谓后现代主义,利奥塔认为,就是异质性向元叙事的挑战,就是元叙事在当代知识状态下的危机。所谓异质性,利奥塔指的是各种知识之间在原则上的根本差异。他认为,科学知识以“真”为原则,但除了真的原则之外,我们还有善、美、愉悦等原则,真的原则不能替代其它原则,也就是说,认知上的“真”不能保证实现社会伦理的“善”。在此意义上,利奥塔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概念,指出人类知识的实际状况是多种不同语言游戏并存,它们各自遵循自己的游戏规则,相互之间无法替代,规则之间无法通约。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利奥塔考察了艺术活动的原则,回答了什么是后现代艺术这个问题。
说到后现代主义艺术,一些流行的见解认为后现代艺术追求大众化和商业成功,它放弃崇高,追求单纯的愉悦感;后现代艺术常常采用杂揉与拼接的手法,以表达自我、主体、本质的消解;还有,后现代艺术充满了平面感,在深度被消解后,后现代艺术已不需要解释,它只要求体验作品本身;而随着现代工业技术和批量生产的长驱直入,“复制”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之一,等等。利奥塔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界定不是描述性地谈论后现代艺术的种种特征,而是试图借助于他的后现代哲学,揭示后现代艺术的实质。
他说,后现代艺术就是“用表现本身展示不可表现性(puts forward the unpresentable in presentation itself)”。(注:J-F.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1984,第81页。)围绕着这个界定,他重新阐释了康德的崇高美学和先锋派艺术的意义。对很多读者而言,利奥塔的论述比较艰涩,本文无意条分缕析地全面叙介他的理论,而是尝试从他的后现代哲学和后现代知识分子理论入手,揭示所谓不可表现性的真正内涵。
二、后现代艺术家的责任
如上所述,利奥塔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元叙事的解体,被统合在一起的知识分散为不同的语育游戏,知识原则呈现为多样性和异质性。结果是,认知主体消溶在这些语言游戏当中,而不是像在元叙事体系中那样能够统摄全局,全知全能,普遍地把握认知对象。因此,元叙事的解体蕴含着“普遍性主体”(a universal subject)消失的结论。基于这个前提,利奥塔重新考察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理论,给知识分子以新的定位。
所谓现代知识分子理论,是指萌芽于近代启蒙主义时期、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概括知识分子群体本质的理论。在法国启蒙主义时期,《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们既是新型知识的代表,也是社会良知的代表,他们起到开发民智、引导人民的作用,这种知识与社会责任的最早联合,典型地体现在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伏尔泰身上,他被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初原型。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社会学的日趋成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受到关注。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提出了有关知识分子的著名论述。他认为,西方宗教的衰落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原来相对封闭、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解体,在思想意识上,西方社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曼海姆认为,唯有知识分子不隶属于任何阶级,因此,他们有更大的自由选择自己的立场,更容易摒除门户之见,形成对社会更普遍、更全面的认识。也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这一功能,他们被看作是社会的良知,是“漫漫长夜的守更人”。(注:Karl 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1940,第143页。)
在现代法国,哲学家萨特同样提出“介入”哲学,主张知识分子介人到社会生活当中去,他说“知识分子就是那种关心自身之外事务的人”。(注:J.P.Satre, Plaidoyer pour l'intellectual,转引自Intellectuals: Aesthe-tics,politics and academy,1990,第xv页。)“自身之外的事务”就是指知识分子专业领域之外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干预生活,成为社会公众的代言人。
在这一理论传统中,知识分子被看作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遵循某种普遍的价值观,全面认识和把握社会,指出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自六十年代起,这种现代知识分子理论受到后现代哲学家的批判。法国哲学家质疑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这种普遍认识能力。1984年,利奥塔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的坟墓》一文,直接了当地宣布“普遍的知识分子”已寿终正寝。
那么,后现代主义所设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由于不同的知识原则不能通约,知识分子也会受到其知识领域的囿限。简单说来,就是在某一领域获得成果的知识分子并非自然而然地在另一个领域享有权威性。例如一个好作家并非一定能够很好地承担对作家协会的管理,同样,一个原子物理学家并不理所当然地是公众政治生活的向导。一句话,知识分子必须对自身责任的范围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不要妄自扩大自身的责任领域。
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艺术家有自身的责任。利奥塔认为,与追求真理、探索真知的科学家不同,艺术家则要创作,而且是纯粹的创作,它不为政治理想服务,也不为党派而生存,它甚至不该受公众接受水平的左右。利奥塔说:
真正的艺术家、作家或哲学家的唯一责任,是回答“何为绘画、写作、思想?”这一问题。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你的作品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有权利、有责任不去理睬这种反对意见。他们的接受者不是公众,我想说,甚至不是艺术家、作家等群体。说实话,他们不知道谁是他们作品的接受者,艺术家、作家等面临的状况是:把一个“讯息”抛入虚空之中。他们也并不清楚了解谁是他们的评判者,因为他们在创作中同时也在质疑公认的绘画、文学评判标准。……我们说他们在进行实验,他们根本不想培养、教育或训练任何人。……他们不需要认同于一个普遍的主体并承担起人类集体的责任,才能负起“创作”的责任。(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集》(包亚明主编,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8页。)
也就是说,后现代艺术家的责任,便是忘却公众,转向对艺术本身的追问。当我们回眸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的更迭起伏时,不难看出利奥塔是在总结这一发展过程,并将之定格为一种艺术观念(注:需要说明的是,利奥塔认为现代性(modernity)与后现代密不可分,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性体制性地、不断地孕育着后现代性。参见J-F. Lyotard,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1991,第25页。)。从西方美术的发展来看,20世纪初的先锋派美术为绘画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它不再是表现什么,而是如何表现。这一课题导致表现形式的探索,而每一次探索又使人追问什么是绘画的本质。从印象派到野兽派,从立体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从画框内的革命到画框外的实验,从静态的表现到动态的行为艺术,面对毕加索对描绘形象的超越,面对杜尚搬进艺术馆的工业制品,人们不禁要问:绘画究竟是什么?西方现代文学也走着一条相似的道路。从意识流小说到现代派诗歌,从艾略特的《荒原》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原有的文学写作观念一再受到冲击。
利奥塔把形式上的探索与实验看作后现代艺术的真谛,因此格外重视先锋派艺术。对利奥塔来说,先锋派艺术是指所有体现实验与探索精神艺术创作。利奥塔指出,先锋派艺术是没有观众的,它是在没有接受者的约束下进行的“艺术语言的实验”。利奥塔之所以完全否认先锋派艺术有任何接受者,是因为如果设定了接受者,就意味着设定了某种价值判断标准,设定了艺术家与其接受者的趣味或观念的共同体。那么,这个接受者就不仅仅是一个观众,他在深层意义上实际隐喻着普遍性主体的功能。
在元叙事解体、普遍性主体消亡的前提下,先锋派艺术必须切断与公众的联系,只能是“孤独的、独身的”。(注:J-F.Lyotard, Just gaming,1985,第10页。)先锋派艺术不迎合任何观众的趣味,不认同任何判断标准,不追求与社会生活结合为一体,也不追求商品的流行性,这种孤立绝缘的状态使先锋派艺术具有非整体的、零散的和断裂的特性。利奥塔把这种非整体性看作是治疗西方当代平庸文化的一剂解毒良药。
利奥塔对当代西方文化有着独特的观察。他认为,当代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在放弃实验精神。不断出现的新艺术潮流,不管是新表现主义还是超先锋主义,都屈从于流俗趣味的压力。先锋派的遗产遭到清算,它的独立品格被遗弃。趣味上的折衷主义正在侵蚀当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使它屈从于现实的价值观。这种趣味上的庸俗化实际上受更深层原则的驱动。利奥塔指出:
折衷主义是当代总体文化的基准点:人们听雷盖(牙买加民间音乐,20世纪60年代中期始流行),看西部片,午饭吃麦当劳,晚饭吃地方菜,在东京用巴黎香水,在香港穿“怀旧式时装”,知识变成了电子游戏。折衷主义作品与公众一拍即合。艺术成了平庸之作,迎合取悦资助人的“趣味”。艺术家、画廊老板、批评家和公众都安于“什么都行”,这是一个懈怠的时代。(注:J-F.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第76页。)利奥塔指出,这种“什么都行”的折衷做法事实上是受消费原则支配的。它缺乏审美标准,但可根据产出的利润来评价作品的价值。不管是什么倾向和需要,只要它们具有购买力,这种折衷主义都会去迎合,就像资本迎合所有“需要”一样。利奥塔将这种情况称为“金钱现实主义”。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他把先锋派的孤立绝缘状态看作是摆脱平庸文化现实的途径,它可使艺术跳出供需关系的左右,通过对“什么是艺术”的追问,达到解构现实整体的目的。这在客观上构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三、什么是不可表现性?
后现代艺术家对何为艺术的追问是一个不会终结的过程,那么是什么东西推动着这一追问不断继续呢?利奥塔说:“我认为正是在崇高美学中现代艺术(包括文学)找到其动力,先锋派逻辑找到其公理。”(注:J-F.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第77页。)利奥塔这里说的崇高美学是指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崇高感的论述,而“不可表现性”(unpresentable)便是他所说的动力或公理。由于不可表现性直接与康德的崇高美学相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康德美学的有关内容。
我们知道,康德提出了“美”和“崇高”两个美学范畴。所谓美,如“花,自由的图案,无谓地彼此缠绕而称作簇叶饰的纹线”,(注:康德:《判断力批判》(1987),商务印书馆,第44页。译文有改动。)给人带来的是知性与想像力的合谐一致,其中,与知性相对应的是概念能力,与想像力相对应的是表现(present)能力,即赋予材料以形式的能力。因此,美感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使人产生优美、愉悦之感,但在崇高感中,想像力遭遇到无法把握的巨大,在无限、绝对的数量与力量面前,想像力提供不出相应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康德引入理性理念——想像力在崇高对象面前的挫败感“在我们内心唤醒了一种感觉:我们内心拥有一种超感性的力量”(注:康德:《判断力批判》(1987),商务印书馆,第89页。译文有改动。)。这种理念要求把无限的力与量作为一个整体把握。康德说,想像力的无能给我们痛感,但理性理念对整体的要求和它所蕴含的使命感、道德力量又给我们以快感。因此,与作为单纯愉悦的美感不同,崇高是痛感与快感并存的矛盾情感。如果说美感是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那么在崇高感中,内容则大大超出形式,表现能力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因此,康德指出,我们可以理解无限大或绝对的力量,但却无法在有限的时空中再现它们。但同时他也指山,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暗示它们的存在,这个方式就是“负表现”(negative presentation),如犹太教禁止偶像崇拜,将视觉表现几乎降至零点,通过这样的“负表现”,它召唤对神明无限性的沉思。
利奥塔的“不可表现性”正是来自康德对崇高的分析。利奥塔说:“理念的对象是不可表现的,人们无法援用例子、事件甚或象征来显示(表现)它。宇宙是不可表现的,人性、历史的终结、瞬间、空间和善等等概莫能外。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的绝对。倘若表现它们,就会把它们相对化,把它们置于表现过程的情境和条件下。所以说表现不出绝对本身。但是人们可以表现出存在着某种绝对。这就是‘负’(康德也说‘抽象’)表现。自1912年以来,‘抽象’绘画的潮流正是应合了这种用可见的形式间接但又明白无误地暗示出不可见性的要求”。(注:J-F. Lyotard,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第126页。)
在利奥塔看来,抽象的形式正是一种间接的暗示方式,它告诉我们在肉眼目睹的形式中存在着一种无法表现的东西。现代文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利奥塔在阐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时说,“到乔伊斯写作《尤利西斯》时,艺术家和作家已经知道(当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写作的关健不是创造美,而是见证那个吸引我们的声音,它在人中间,但却超越人、自然以及两者古典式的和谐一致。”(注:J-F. Lyotard, Toward the postmodern, 1993,第198页。)在这里,所谓超越人、自然及两者和谐的那个“声音”正是理性理念的对象,即绝对的声音,它超越一切表现形式,是不可表现的。利奥塔一再强调后现代艺术主要关心的不是美,而是崇高感,即表现不可表现性。
利奥塔说,后现代艺术“拒绝优美形式的抚慰和趣味的一致——这种一致会使公众共同缅怀那不能获得的东西;它寻求新形式的表现,目的不是获得愉悦之感,而是产生一种更强烈的不可表现感。”(注:J-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第81页。)所谓“不能获得的东西”指的就是对无限性的克服,对整体性的把握。在对崇高的分析上,利奥塔基本采纳了康德的理论,但在对理性理念的态度上,他们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康德论述崇高的目的是要找到从审美向道德的过渡桥梁。因为,快、痛交织之感是道德情感的特征,而且当想像力无法把握对象时,理性理念被引入进来,起到超越无限,克服想像力的局限的作用。这种克服不是在认知意义上完成的,而是体现了一种道德意志,因此,康德在这里所说的理性理念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理性。这样,崇高就完成了从情感向道德、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理性对整体性的把握成为崇高感的核心内容。
但在利奥塔看来,这个整体性是“不能获得的东西”,因此他理解的崇高不是理性对无限性的超越与克服,而是面对理性对象时想像力的无奈,表现力的无能,是不可表现性。对康德来说,在理性的召唤下,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整体性;但利奥塔却对理性把握整体性的过程不置一词,他只是一味强调想像力向无限的逼进,强调不可表现性,从他极力推崇先锋派艺术的非整体性特征来看,他对建构整体性的理性是持否定态度的。
事实上,利奥塔对元叙事和现代知识分子理论的解构,都是针对整体性来的。元叙事将各种知识统合在共同的原则之下,将分散的知识组成有机整体;而现代知识分子理论的普遍性则为知识分子整体把握世界提供了前提。因此元叙事危机、普遍知识分子的消亡和不可表现性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对整体性、理性的根本怀疑。这种怀疑尽管是在哲学层面上展开的,但却是利奥塔政治信仰转变的结果,也是他新的信念所在。
利奥塔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与工人运动。但到六十年代中期,由于缓和的阶级矛盾不断推迟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工人运动的前景晦暗不明。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政治生活曲折重重。这些情况导致很多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产生动摇。此外,法国学界曾就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展开争论,利奥塔认为无法从理论上圆满论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正义性。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人有权获得民族独立,但另一方面,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通过独立而成为新统治集团的阶层与民众利益不可调和地相冲突。利奥塔认为没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能够涵盖不同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由此,他对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产生怀疑。对他来说,以资本主义为对象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不过是在人类、理性或创造性名义下,或在第三世界、青年学生名义下进行的象征性抗议罢了。(注:J-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第13页。)
因此,在利奥塔看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全系于对体系性、整体性的逃离与反叛。通过对形式的探索与实验,先锋派艺术正是起到了这种作用。实际上,这是利奥塔放弃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个无奈的选择。利奥塔让知识分子放弃干预社会生活的使命,让先锋派艺术家背弃公众,在“不可表现性”的驱使下,以不断的形式创新,突破资本力量与利益原则的整合,突破消费原则带来的文化折衷状态。但从他的理论结果来看,先锋派艺术家远离公众,远离社会生活,放弃对共同社会理想的认同与追求,在他们的形式表现中剔除了现实的社会内容,这样,便无法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剥削关系、统治关系。最终,形式探索成为趣味的实验,它不可能构成对现实社会真正意义的批判和解构。事实上,不管如何远离社会生活,先锋派艺术家都处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单纯的逃避只能使他们的趣味实验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杜会的又一处“无害的”文化景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