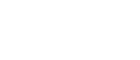中图分类号:D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5057707
Abstract:Gay politics experience moral theology,medical discipline and gay liberation,and dualism is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ay theories,queer theory played a crucial role,but also has tensions.“Red queer theory” combines Marxism's economy-class analysis and queer theory,and it is the supplement and critical re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queer theory.By virtue of this critical perspective,reconsider the gay identity politics,“closet” political theology and the essence of gay oppression.
从跨文化的历史证据来看,同性恋行为与欲望在人类的性态中根深蒂固,在不同的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被建构着。自19世纪末以来,性态逐渐成为大众窥视、医学凝视与法学监视的对象。同性恋研究本身也得到发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日益意识到性范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同性恋去病理化和非罪化的同时,同性恋权益运动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现如今,同性恋、酷儿、跨性别、双性恋、易性癖和阴阳人等已成为广为人知的术语和知识对象。
20世纪80年代后期,酷儿理论①的出现使曾不幸被污名化的性身份成为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入口。[1]酷儿理论最初对反思与重构传统的同性恋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理论本身也观点芜杂,内部充满竞争和矛盾。红色酷儿理论对酷儿理论(尤其是酷儿左派)持激烈批判的立场,但并没有彻底摒弃酷儿理论,而是更多地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方法。是对酷儿理论的补充和批判性重构。本文主要论述当代的同性恋政治学,探讨红色酷儿理论对身份政治、“橱柜”政治神学以及同性恋压迫(恐同症)的反思与批判。
一、同性恋政治的谱系学
早期?范西方同性恋关系和实践的主要是宗
教话语。在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传统的分裂使欧洲难以继续维持一种建立在独特的超验价值观基础上的公共行为规范,神圣与罪恶的宗教观逐渐不再成为公共领域中关于性行为的定义方式。到了20世纪初,科学的价值观(尤其是医学)取代了基于神学原则的共识,对灵魂救赎的关注越来越少,而对身体及其健康的关注则越来越多。约翰?博斯威尔(J.Boswell)认为,这种转变最终导致中世纪关于同性恋行为的渎神思想被转变成疾病与变态的观念;从此,这种病态以各种方式被概念化为遗传学的“特征”、心理学的“症状”以及“倾向”或“偏好”,[2]160这些本质性的术语表明同性恋是固有的属性而不是外来的,它将欲望描述为弗洛伊德式的寻求发泄的力比多(性欲)常量。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同性恋行为在跨文化中普遍存在,但其意义在各种文化中不尽相同,其社会呈现形态各有差异。[3]“Homosexual”这种19世纪的表述被认为过于僵化、武断,无法表达人类性实践和身份的可塑性和多样性。与此同时,通过性研究者和活动家的不断质疑,“异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或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被动摇,虽然它仍然是性态的支配性模式。
性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同构原则。类似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异性恋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表达形式,它赋予异性恋优越的特权。异性恋主义通过各种主体化过程而产生恐同症主体,尤其是自我憎恨的同性恋者,并最终生成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所谓的“强制性异性恋”。[4]在异性恋的思维模式中,认同和欲望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自我认同为某种性别,就必须对另一种性别产生欲望;而同性恋者消解了这种想当然的关联性。在无处不在的异性恋主义铁幕的笼罩之下,同性恋者在同性欲望、家庭责任、出柜压力、恐同症、社会污名以及对艾滋病的恐惧中痛苦地挣扎。同性恋欲望如异性恋欲望一样,只是对欲壑的一种任意划分,而欲望本身是多形态的和未分化的,在这种意义上,“排他性同性恋”的表述是一种想象的谬误、误识或意识形态的错觉。在现代大多数西方文化中,性取向被理解为“同性恋-直人”(gay-straight)的二分法已经很少见。许多学者的立场与研究取向,诸如“同性恋角色”[5]、“内部/外部视角” [6]等,都是为了消解“同性恋-异性恋”的二元对立。同性恋仅是诸多性少数族群中的一种,此外还有那些自我认同为“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是异性恋”(比如“无性”)的人,还有诸如双性恋、跨性别者、“易装皇后”(drag queens)、虐恋和恋物癖者等。显然,“同性恋-异性恋”这种二元对立式的划分忽略了性态与社会性别的多样性。人类性本能的对象和满足方式可以非常广泛和多变,其对象可以是恋人(包括恋童、恋老等)、恋动物、恋衣物、恋尸和恋脚等;其满足方式也可以从露阴(癖)、偷窥(癖)到各种类型的性行为以及性施虐、受虐、奸尸、兽奸和排粪淫等。此外,性欲和性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协商的、持续终身的过程。任何固定的分类体系与框架会限制个体实现完整、真实的自我认同。 同性恋理论家对诸如主体/客体、内在性/外在性之类的界限提出了疑问,尤其是对自我/他人的二元论提出挑战。[7]43性身份并不必然附属于自我,也并不一定存在于自我内部并能够表示自我。同性恋身份或角色也并非是结构化的,诸如主动/被动、男子气概/女性气质以及男人/男孩等都是过于绝对和简单的划分。在周华山看来,如果将同性爱欲视作一种表演、一种行为、一种社会角色、一种可能性和一种任何人都可以经历和体验的潜在特质,那么在“同性恋-异性恋”之间想象的“我们-他们”的二元论和恐同症将会失去其坚实的基础。[8]任何一种身份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个体的身份无法从其性别、种族、性态、民族、阶级地位以及年龄等要素或属性中剥离开来。因此,不能将“同性恋”与其他身份构成或差异类别分开进行考虑,也不能脱离意识形态背景而对“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的类别进行概化。诸如“gay”“lesbian”这样的新身份类型也不会自然而然地比“homosexual”这样的陈旧身份更具适应性和展延性。[9]1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同性恋活动家认为对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界定可能反应了一种强烈的政治意愿,他们“欲把同性恋社群凝聚在与异性恋社会完全对立的一种明确的、排他性的身份认同之下”。[10]6在他们看来,同性恋族群的自我认同与边界划分是社会行动的动员策略。
杰弗里?威克斯(Jeffrey Weeks)认为,同性恋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是探讨特定社会中针对性行为之独特控制形式的各种条件。[11]81在建构主义范式的主导下,人们主要关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制造”同性恋-异性恋主体的过程,这使我们最终离开本体论领域(即同性恋是什么)而进入到社会和话语形成的领域(即同性恋身份是如何形成的)。[12]建构主义揭示了同性恋研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偏向。然而,在斯蒂文?赛德曼(S.Seidman)看来,建构主义范式并没有将这种批评意识运用到自身的话语中。[13]解决这种困境的可能途径之一是采取后结构主义的策略,后结构主义倡导从一种以个体作为主体创造自身的人文主义视角转向一种结构性的秩序,从抵制性的同性恋主体转向分析同性/异性符码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关于观念、知识和文化的结构模式。[12]1920世纪90年代的酷儿理论建立在与异性恋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基础上,这种具有高度涵括性和包容性的理论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性学思想。酷儿理论将异性恋-同性恋二元论看作是一种建构自我、性知识和社会机构的总体性压制框架。这种与性系统相关的二元划分的权力/知识体系产生了僵化的心理和社会边界,并进而生成统治制度和权威等级组织。[12]酷儿理论将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以及其他性身份都视为具有历史偶然性的范畴,它们都不是超历史的现象。这种观念反映出对原先性形态分类学的拒斥(如同性恋、异性恋、恋物癖、鸡奸者等),这些性类型是通过19、20世纪之交的性学话语而确立的。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代表了西方性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之前被法律和医学/心理学诊断的性少数群体和越轨者被塑造成彼此竞争的话语群体,并设法重新协商其身份。[14]酷儿政治成为一种后现代版本的身份政治。
二、“橱柜”政治神学
学界对“橱柜”的发展阶段并没有一致的观点,这里我们采取其中的一种划分法。第一个阶段是从1969年的“石墙骚乱”到70年代。这十年间,“橱柜”是强制性的、迫不得已的避难所,同性恋活动家对普通同性恋者进行施压,要求他们“出柜”(coming out)。该时期作为同性恋解放的出柜与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和资本扩张密切相关。第二个阶段是经济大萧条时期,从1973年石油危机到1993年税法,这20年间美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变化,长时期的经济繁荣结束,出现经济不确定性和倒退。第三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酷儿理论的发展,早期对橱柜的理解被逆转,橱柜成为一种“至上的”愉悦空间,逼迫他人出柜反而抑制了橱柜里能够享有的愉悦。酷儿理论宣称橱柜是一种“无法被描述的欲望”和“游牧主体的享乐场所”。[15]2
在酷儿左派看来,“从橱柜中走出来”是一系列主体性变化导致的结果,同性恋者等性少数族群的解放是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者发展出反话语和调动新的策略、战术来开拓同性恋/酷儿/双性恋等的空间实践的行为结果。同性恋解放运动注定会使同性恋者出柜并提出权利诉求,这被塑造成同性恋主体“创造历史”的传奇。与这种传统自由观和近代葛兰西式左派运动的立场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唐纳德?莫顿(Donald Morton)认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酷儿/双性恋等公民与异性恋公民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一种正在浮现的意识问题,也不是反历史的相互关系,而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的结果”。[15]8橱柜是工资-劳动制度的附属物,在工资-劳动制度下,阶级利益总是优先于文化差异。莫顿认为橱柜并非是一个自我迷恋的、具有自主性的地方,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由资本运作规律构成的空间。酷儿理论家声称在“后橱柜”时代,橱柜不再是藏匿地,而是“福地”。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平等的恶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酷儿左派将它们的意识形态与“崇高的橱柜”进行新的结合,从而宣称不再需要出柜的意识形态。这导致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和酷儿越来越深地陷于追求享乐-满足的“无为主义”(quietism)。莫顿指出,酷儿左派的“出柜”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解放”,他们将阶级弃之不顾,宣称同性恋问题如同种族、性别问题等一样,可以通过将所谓的“民主权利”扩大到现行经济制度下的不同社会边缘群体而得到彻底的解决,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忽略了这些权利。酷儿左派将马克思主义贴上“经济还原论”的标签,并且视之为民主制度的反对者。
现代主义视角下的橱柜政治将出柜置于家庭和亲属关系变迁的框架内,将同性恋经历统一于现代主义的叙述之下,从而夸大了出柜的政治效果与个体意义。这种历史与现实背景下的出柜不再是一种个体解放的经历,而是一个遵从并使之符合既存的中产阶级规范的过程,它不仅拒绝先前的工人阶级背景,而且甚至拒斥同性恋者在出柜前已经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和性网络。这样的出柜使得都市生活原本可以保证的匿名性与远?x监控从而确保自我之充分发展的条件难以付诸实现。[16]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橱柜政治充斥着不平等的隐喻,出柜成为享有特权者的实践,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企图表明在完全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剥削和性压迫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在后现代与全球化时代,性经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与日俱增,将出柜视为普遍性的同性恋身份之必要组成部分之前,应考虑对同性恋者自身而言,出柜是否可行、是否能够承担其结果。斯蒂文?赛德曼指出,不应该仅仅因为橱柜维护了异性恋主义的权力并可能形成自我憎恨的同性恋者而简单地视之为消极的和压迫性的。[12]168橱柜实践也可以被视为积极的,它们可以避免由于身份暴露而带来的风险,创造“保护性的”社会空间,从而允许个体塑造同性恋自我,并在异性恋与同性恋世界之间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同时也不排除出现一种在不出柜的前提下实现性解放的可能性。如果同性恋身份变得日益常规化,那么有关出柜的叙述将会变得更普遍,甚至最终消失。[17] 同性恋压迫和同性恋自我异化的另一种形式是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商品化。红色酷儿理论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酷儿政治已经将自己出卖给了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对同性恋者而言,“独特的同性恋行为是一种强迫性消费”。消费主义模式下“同性恋解放”具有瓦解的作用:自我认同的同性恋群体希望享受愉??、被阿谀奉承,而不是被批判。他们拒绝思考阶级、种族和性别歧视问题,而沉迷于商品化和消费主义,并自以为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事实上,“同性恋解放只为那些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白人男性在主流社会中进一步获得了空间”。[15]5莫顿认为,同性恋作为“生活方式”是一种基于阶级差异的解释,大多数同性恋普罗大众无法负担和参与这种“生活方式的市场”。这些酷儿投机主义者实际上是在出售“时髦的生活方式和现成的社会身份”,[15]19他们将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表征为一种“特殊的消费者”群体,以试图“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酷儿可以摆脱与污名之间的联系。
红色酷儿理论认为传统的身份政治无法超越自我,因而不可能对资本主义构成集体性的挑战。身份政治将身份认同的要素,诸如国籍、种族、性和性别等,看作是固定的、本质的决定因素。[18]90尽管身份的自我定义是任何解放运动必要的起始点,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只需稍微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就可以看到身份政治内部隐含的矛盾、冲突与分化。在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特殊背景下,基于身份一体感的女同性恋政治事实上割裂了不同的女同性恋亚群体,“女同性恋”实际上成为白人女性和中产阶级的代名词。乔纳森?劳施(Jonathan Rausch)也指出,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同性恋者比工人阶级和穷困的酷儿具有更高的社会可见度,工人阶级和穷困的同性恋者并不是同性恋运动政治动员和以报纸、杂志等为媒介的消费主义之对象。那些中产阶级的酷儿参加各种同性恋共同体的晚宴、鸡尾酒会和研讨会等,只有他们才是同性恋事业的争取对象和商业的消费主体。[22]256此外,女性主义者和性工作者在色情政治、卖淫和性享乐等方面也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于狭隘地关注特殊性而造成的。争论的一方认为色情和卖淫是男性性压迫和暴力对待女性的场域,因此必须通过不同的管控措施严加禁止,甚至不惜使之罪化。而另一方则认为这违反了性工作者的身份认同、选择自由、自我表征和公民权,是对公民追求享乐和性自由权利的不必要限制。他们试图在公民社会的话语内将性工作正当化,坚持与性工作者的人身相联系的财产权和自决原则,认为性工作是象征着选择、欲望和自主权的实践。[23]296-298
因此,身份政治本身是充满悖谬的,它的存在以个体身份认同的碎片化和分化为前提。身份政治通过公开否定跨越种族、性别和性的身份而导致集体运动的碎片化,因而无法提供一种将斗争联合的理论和经验。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和精力、原子化人们的努力、抽空对社会现实的理论和观念的解释。因此,女性主义和当前在同性恋解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无法形成一场持久的运动。[24]17后结构主义承认身份会产生差异政治,因而它试图以一种多元的、且具有弹性的“差异”观念来代替“身份”,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克劳德将这种所谓的差异政治斥为“尚未克服唯心主义的本质主义,将身份政治的逻辑碎片化”。[18]91同性恋的解放需要放在异性恋的统治结构中进行思考。无论是父权制还是强调核心家庭之首要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对同性恋的压制和管控都是异性恋社会强调、重申和再生产自身的重要方式。 [6]恐同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生产关系中产生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23]137它既是工资-劳动体系中不平等的结果,也是其合法化的方式之一。在莫顿看来,“只有结束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消除同性恋恐慌”。[15]2
五、结语
本文论述了同性恋身份政治和“橱柜”政治神学,并借用红色酷儿理论批判了传统酷儿理论;简要梳理了同性恋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即从早期的道德神学到后来的医学规训再到后来的同性恋解放政治,其核心是解构性学领域二元对立的神话,这种二元论是建构同性恋类别的基础,也是传统身份政治的根基。橱柜政治与主体政治、同性恋解放运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本文也探讨了红色酷儿理论的批判性话语以及未来同性恋解放的可能性。本文既是对酷儿理论的批判,也是对当代西方同性恋政治学的反思。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包括霍华德?贝克尔的标签-互动理论、麦金托什的同性恋角色研究、欧文?戈夫曼的污名研究以及约翰?盖格农等人提出的“性脚本”理论以及福柯针对性史的研究。80年代末,酷儿理论又逐渐成为同性恋研究的重要视角,它关注性身份中的差异政治,解构压制性的性政权及其话语生产体制,产生了大量颇具启示性的文本和解放性的实践。红色酷儿理论则是对传统酷儿理论的进一步批判性重构。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和强制性异性恋统制下,要获得真正的同性恋解放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