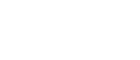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6??0062??0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08YBA058)
作者简介:佘小云(1971-),女(侗族),湖南靖州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著名宗教学专家辛之声提出了“大宗教”的概念,认为民间信仰具有宗教性,应该努力运用民间信仰的神圣性和文化正统意识,使民间信仰进入“宗教生态平衡系统”建设,并开掘和发挥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使其名正言顺地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1]
侗族是聚居于湘、桂、黔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少数民族,人口200多万。侗族民间信仰的内容很广泛,从信仰对象来看,主要有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古杰崇拜、神明崇拜等,这些信仰意识外化为一定的信仰行为和活动,主要有祭祀、巫术、占卜、祈祷、看风水等。这些信仰及其活动从原始社会传承至今,仍然为广大侗族民众信奉和实践,必然有其存在的功能和价值。本文以湖南侗族为例,探析侗族民间信仰在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社会系统正常运作以及调节信众心理、促进信众社会化、促进交往娱乐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思索其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作用。
一、社会控制功能
社会控制指人们依靠社会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形式和方法,以一定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施加影响,以协调个人和社会及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也就是对个人或集体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使其符合社会传统的行为模式,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的过程。社会控制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是行政、法律、道德、宗教手段。[2]侗族民间信仰没有发展成为完善的制度宗教,但是作为一种准宗教,其从宗教的维度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
(一)侗族民间信仰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不成文的程式化规矩属性,约束信众的意识和行为
侗族民间信仰没有严密的组织团体、严格的教义教规、固定的神职人员,也没有绝对固定的祭祀拜谒时间,具有松散性的特点,但也形成了一系列不成文的程式化规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相对固定的祭祀时间。侗族祭祀祖先的时间相对固定。清明节、鬼节是侗族祭祀祖先的固定节日,之外各姓氏还设有特定的宗祖祭祀日,一年或几年一次举行祭祀活动,如会同沙溪乡杨氏每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其祖杨再思的忌辰都举行“抬太公”活动,祭祀杨氏宗祖杨再思,此外各家各户逢年过节都必须祭祀祖先;萨崇拜(侗族的始祖崇拜,侗族以“萨岁”为民族始祖)的祭祀时间也相对固定,农历初一、十五或逢年过节,各家各户都要自行祭萨,集体祭萨一般一年或三、五年一次。第二,相对一致的祭祀仪式程序。如侗族各地区的萨崇拜活动虽没有形成固定的仪式程序,但具有相对的一致性:修建萨崇拜活动的祭坛――萨坛,一般包括接萨、安萨、祭萨几个分支仪式,各仪式的具体程序也相对一致。[3](P35 ̄39第三,信仰活动中有必须遵循的规范和禁忌。在萨崇拜活动各分支仪式语境中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和禁忌,例如,修建萨坛时,必须封寨,不允许外人出入,全寨各家各户必须熄火,出嫁的女子必须接回,孕妇不得参加祭祀活动,一般不到他寨萨坛祭萨,祭祀场所不得大肆喧哗等。[4](P107 ̄124)侗族民间信仰活动中的这些程式化规矩,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必须遵守,但是在传承中代代相传,约束着信众的行为和意识,调节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
(二)俗信和禁忌是支配侗民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一些原始民间信仰在长期民间传承中,逐渐丧失了神秘色彩,而转化为一种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都保留了下来,并对人们的生活起着一定的支配作用,这些风俗习惯就被称为俗信。[5](P238)俗信因其千百年来沿袭的惯制的特点,成为约束人们言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具有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禁忌指出于顾忌某种人们相信的非现实的神秘力量,害怕招致惩罚和灾难而禁止某些言行的现象。俗信和禁忌都是世代相传的。侗族俗信禁忌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从纵向来看,侗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始终处于先在的俗信禁忌的约束之下。从横向来看,俗信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处不在。例如,侗族建房有诸多习俗:“房屋进深、开间、高矮尺寸的整数和尾数都要套上八的数字……当建房竖起屋架后,要在中堂顶上安装梁木,选择做梁木的树,最好是‘母子木’,即同根而生的多干树……砍梁木树时不能让树干倒地,用肩接住,抬梁木不能换肩,抬回工地后架在木马上……上梁时要在梁上抛宝梁粑和糖品……”[6](P249 ̄250);再如,年初一至初三不得下地劳动,上山砍柴忌高声大叫、粗言秽语等。这些俗信禁忌就如同最原生最特殊的规范形式,个体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中习得,并遵照执行。
(三)侗族民间信仰与其他意识形态交织,维护社会稳定
首先,民间信仰渗入到政治活动中,使侗族传统社会表现出“政教合一”的特点。侗族传统社会的补拉组织、村寨组织、款组织的“行政权威”分别是族长、寨老、款首,他们都是以民选公推的形式推举出来的,负责处理对内的日常公共事务和对外的交涉。他们在行使日常社会管理职能时,常邀约神灵到场,使其行政事务渗入民间信仰的神秘色彩,如村寨间的芦笙大赛要请萨、祭萨,修建公共设施也要先祭萨,把村寨的世俗公共事务置于超自然神灵的观照之下,也就是把世俗世界整合在神圣世界的视域之中,这样族长、寨老、款首等首领的“行政权威”涂上了不可抗拒的神圣色彩。同时他们也直接负责主持组织内部的集体民间信仰活动,如祖先崇拜活动、萨崇拜活动等,行使宗教权威的职能,可见侗族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是基本整合的。
其次,侗族民间信仰具有道德化属性。侗族信奉的神灵中有一类是基于人类自身升格而成的神灵,包括将祖先、古杰、各行业的杰出人物等神灵。能升格为神灵的人物,一般都具有良好的人格精神和品德魅力,或者勤劳智慧、勇于开拓,或者公正无私、廉洁自律,或者造福一方、舍己为人,或者善良仁慈、尊老爱幼。这些人本身具有道德的号召力,是后世学习的楷模和道德教化的榜样。对这些神灵的敬畏和崇拜就是一个道德教化的过程,这些道德因素在信仰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信众的道德规范,从而起到约束控制信众行为的作用。另外,侗族民间信仰还是道德控制的有效监督手段。侗族常说“老天有眼”,认为天神默默注视世间一切,每个人的言行都逃脱不了老天的法眼,行善天佑,作恶天罚。再如侗族认为做了坏事会遭天打雷劈,也是相信雷神具有惩恶佑善的特性。民间信仰中这种善恶有报的观念无形中约束了信众的行为,促使人人向善,抛弃恶行,从而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促进和维护社会稳定。在世俗社会,一个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即便触犯了道德规范也不会受到来自外界的谴责,而神灵是一种超时空的存在,作为一种无形的存在,其监督也是超时空的,每个人都时刻处于神灵的注视之下,因此通过民间信仰超时空监督,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力也增添了一定的神秘性,因而约束力更强。
再次,侗族习惯法的制定、宣传、依法判罪都是在神灵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充满了神秘色彩,表现出民间信仰对法律手段的渗透与整合。侗族传统社会并没有出现国家政权机关及警察、法院、监狱等暴力机构,也没有出现现代意义的法律,但是侗族民间自治组织――款组织制定了相关的款规款约,这些款规款约就是侗族社会的习惯法。进行合款活动时,要讲诵“请神款词”,邀约诸神都来参加合款活动,并请诸神见证合款以增加款的神威;款约是众人共议的,议定之后“歃血”表示起誓于天地鬼神祖先前,相互之间要坚守约定,凡触犯则与被杀之牲口一样死去。宣传款约时,有的讲款者就是巫师,讲款时设有神台,而“讲款者一般都站在高高的石台上或板凳上,手中拿一大把用禾杆草或芭茅草挽成的草结。每讲完一条,听众就齐声高呼“是呀”、“对呀”,然后讲款者就将一根草结放在神台上,以示此条已经讲完。”芭茅草在侗族社会是神圣之物,讲款时手拿芭茅草的目的是强化讲款的神圣性和服从的神圣性。讲款活动结束时要念送神款,“内容是宣布讲款活动已告结束,请各位神灵各自归位,并请求永远保佑村寨里的人们,同时也忠告各寨款众要牢记祖先传下来的规章约法。”[7]依法判罪时如果没有达成共识或证据不足,常常采用神判,即通过占卜、捞油锅等巫术来判定当事人是否有罪或如何进行相应的制裁。可见民间信仰始终被整合在侗族习惯法之中,从法律的维度发挥着社会控制功能。
二、心理调节功能
心理调节指通过一定方式把人的心态从不平衡调节到相对平衡,并由此使人们保持积极而稳定的情绪,在心理、生理、精神和行为上达到和谐的状态。社会是由具体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多数社会成员心理的稳定与平衡是社会系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宗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社会个体和群体进行心理调节,借助于超人间的力量,为社会成员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和安全感。”[8](P226)侗族民间信仰是侗族地区的普世信仰,其在“大宗教”语境中发挥着重要的心理调节功能。
当侗族民众面对自我无法解释无法驾驭的人生困境时,向超自然的神灵求助,希冀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战胜困难、摆脱困境、消除病痛,并深信在神灵的佑助之下,一切困境和灾难都可以克服和战胜,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安全感,消除恐惧、无助、不安等不良情绪,进而形成积极而稳定的情绪状态。侗族民众一般把天灾人祸等归结为邪祟所致,常请巫师驱鬼避邪、禳灾去祸。如,村寨不宁,灾祸不断,则往往祭萨扫寨,他们认为对萨不虔诚或者某些地方得罪了萨,都会导致萨不满而离萨堂而去,失去了萨保护的村寨就会鸡犬不宁,灾祸不断,只有接萨归堂并祭萨扫寨驱除邪祟才能使团寨恢复安宁,当寨民认为萨已经生气离萨堂以后,全寨老幼均惶惶不可终日,一旦接萨祭萨以后,才能消除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3](P35)侗族患病也常求助于超现实的神灵,如孩子多病多灾,则祭拜古树巨石为祭父祭母,求其庇佑孩子;多年未育则拜山求子或架桥求子;身患重疾则寻求冲傩、冲关煞等治病巫术。这些治病方式无疑有很浓厚的迷信色彩,但确实存在所求灵验、疾病治愈的例子,其原因可能是患者在巫师的心理暗示下,或者在自我的心理暗示下,认为致病因素已经排除,神灵会庇佑,从而消除了恐惧感和焦虑感,心态趋于平和安定,而心理的良好状态会起到生理的良好调节作用,从而起到了治病强身的效果。[9]
侗族民众在自我努力的预期没有把握时也常求助于神灵,以此规避危机风险,以保证预期目的的实现。如侗族村寨间芦笙比赛,各队均要祭萨,祈求萨佑助比赛获胜;再如,新晃侗族修建房屋要“起水”,祈求神灵保佑建房顺利;甚至象孩子升学或出门务工等事均祈求神灵保佑顺利平安。将自我的生产生活行为置于神灵的关照之下,可以在心理上获得一种被佑感,这种被佑感可以消除自我的焦虑和不安,从而回归正常的心理状态,进而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生产生活之中,这也是民间信仰的心理调节功能的表现。
侗族民众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或发现社会的不公时,会导致心理的不平衡,而自我的理智和实践又不能消除这种不平衡的心态时,于是寄希望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通过因果报应的企盼,希望“老天有眼”,惩恶扬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而把不平衡的心态调节到正常的心理状况。或者面对身体上物质上精神上无法消除的既定不幸和痛苦,将之归结为超自然的命运使然,非人力所能改变,从而坦然接收不幸的人生或命运,以此减轻痛苦、稳定情绪、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这是侗族民众在面对既成事实的天灾人祸时,意识层面的自我解脱之道。
民间信仰活动能激发信众的宗教情感。在各种信仰仪式中,信众与神明沟通,向神明表达虔诚、敬畏、依赖、祈求,并用心体会神的意旨,在这种沟通中,由于信众是认同自己所崇拜的神灵的,在信仰活动场所以及活动过程中,各种信仰象征物,或神灵的物质载体及其现场气氛都使其产生肃穆感、神圣感、敬畏感、虔诚感等,这些情感都有利于心态的平和宁静。另外,民间信仰活动娱乐性特质也有助于调节信众的心理。侗族民间信仰活动充满了娱乐性,是特定信仰圈民众的一次聚会,例如,不管是萨崇拜还是祖先崇拜,都增加了信众的集体交往,密切了信众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娱乐了身心,消除了烦恼,扩大了信众的交际圈,这有助于信众积极快乐情绪的形成。
三、文化传承功能
侗族地处湘桂黔交界的边远山区,其社会发展极其缓慢。改革开放以来,侗族社会虽然逐步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型,但总的来说其现代化进程落后于发达地区,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前工业社会。人们基本生活在依赖经验而运转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自发地依靠习惯、传统、风俗、家规等各种各样现成给定的经验或知识储备、文化规范体系而生存。在这样的前工业社会里,民间信仰是其文化知识体系的核心,民间信仰的习得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和内容。
民间信仰活动是个人习得侗族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个人要在社会中生活,首先要了解人类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和自己所在社会一些最基本的文化。在不发达的侗族地区,对超自然力量的信奉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民间信仰的前喻式传承就是习得民族基本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例如,侗族最主要的信仰是萨崇拜,集体祭萨时,全体寨民要集中到鼓楼前坪讲款,款是侗族社会自发以地域为纽带结成的自治组织,为了团结群众维护村寨利益,款制定了一些乡规民约,这就是最初的款词,后来款词的内容扩大,有赞颂英雄的,有回顾侗族历史变迁的,有关于祖先崇拜、道德规范、文学艺术等各种内容的款词,因此讲款其实就是传承侗族文化最主要的形式,是个体习得社会经验、行为规范、民族知识的重要方式,是获得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除了讲款以外,祭萨时还要讲萨的来源、迁徙的历史、族群分支的由来等,还要弹琶、跳芦笙舞、哆耶等,因此萨崇拜活动也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艺术的一种教育和传承。
民间信仰的习得是把握民族文化的关键。信仰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人们创造了信仰,并以信仰为起点,进而创造了自己一系列的文化。”[4](P7)民族认知的基本方式、民族文化象征体系、民族文化的特质等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都基本可以从该民族的民间信仰中找到原因。侗族认为自然万物皆有神灵依附和掌管,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常祭祀各种神灵,祈求神灵的保佑,这样就形成了侗族超验的认知方式;侗族民间信仰活动“仪式中充满了象征符号,或者干脆地说,仪式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系统[10](P202)”,萨崇拜仪式语境中,物体、行为、关系、事件、体态和空间关系都属于象征符号,都具有仪式语境所赋予的特殊意义,如萨坛象征的是始祖母的坟茔和微观化的神界,而置于萨坛上的伞象征至高无上的祖母神――萨,这些象征衍生出了民族文化象征体系;侗族文化表现为一种母性文化,或称“绿色”文化、“月亮”文化,这也源于其萨崇拜。[11](P233)侗族认为女性是万物的母亲和主宰,因此把母系氏族时期的女性先祖萨岁叫‘萨’,尊其为始祖神和民族保护神,这形成了侗族尊重女性的传统,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不具扩张色彩的阴柔美的文化特质。可见侗族民间信仰孕育了侗族认知的基本方式、民族文化象征体系、民族文化的特质等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都在民间信仰的传承中被信众习得,个体也因此把握了民族文化的关键。
四、社交娱乐功能
首先,群体性的民间信仰活动促进了交往的增加。侗族的民间信仰活动中有大量群体规模的,有的甚至是区域性的全民信仰活动,例如萨崇拜和杨再思崇拜,萨崇拜以村寨为单位举行,全体寨民都参加,如果重修萨坛,则出嫁姑娘也必须接回;而杨再思崇拜最初是会同和靖州一带杨姓的祭祖活动,但后来演变为以侗族为主糅合了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一种跨民族的信仰活动,尤其是靖州飞山杨再思祭祀活动,总是吸引远近各族同胞。再如,一些规模较大的挂众亲活动,甚至突破了区域的局限性,成为涉及面很广的祭祖行为,2009年清明节新晃中寨杨氏举行了祭扫杨天应墓挂众亲活动,参加人员多大200多人,来自湘黔两省,事先严密组织规划,事后还举行了联谊活动。这些集体性的民间信仰活动为信众的群体交往提供了更多机会,在活动中,信众可以面对面地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从而密切了信众的关系。
其次,侗族民间信仰建构了人们日常交流的文化语境。交往是以交流为基础的,而交流是以特定的文化背景为支撑的,亦即交流者之间必须有共同的文化语境,交流才可能实现。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其信仰文化,因此融洽而深入的交流必然建筑在共同的信仰背景之上。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侗族社会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使得侗族社会还处在强大的自在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民众进行着以家庭为单位的以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其交往圈狭窄而封闭。在这样的交往圈中,传统的习俗、信仰等常常是人际间的主打话题,而信众也在共同的信仰所营造的交流氛围中获得彼此认同的情绪体验。比如,祭拜古树、巨石等民间信仰活动是个体单独进行的,人际间并没有因此增加了交往接触的机会,但由于崇信相同的神灵,因此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信众会彼此交流与神灵沟通的感受,或者分享敬奉神灵的灵验经验等,这些基于共同信仰的话题也促进了交流的深入,而交流的深入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从而有助于消除人际间的隔膜,化解人际间的矛盾。
再次,侗族民间信仰具有世俗化和娱乐化的特点。侗族民间信仰的神圣性不强,有别于以彼岸世界为现世人生价值目标的宗教,其根本出发点是为现世的美好生活求福佑,而且其世俗化、娱乐化倾向明显。一些集体性的民间信仰活动大多带有民俗的性质,在活动进程中,信众在准宗教情怀中混杂了娱乐的心态。例如侗族地区极为普遍的“挂众亲”活动,清明时节,补拉成员前往宗祖墓地祭扫,既是追思怀远,也是亲人团聚、踏青游山,大型的挂众亲活动更带点同姓补拉集体联欢的性质。再如,一些祭祀宗祖活动演化成了宗祖祭祀节,不仅参与者抱着娱乐的心态,而且还吸引了大量的围观者,具有娱乐他人的性质。这些娱乐化的信仰活动不但丰富了信众的生活,愉悦了信众心理,也促进了人际间的交往。
当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侗族民间信仰也必然存在某些消极的负功能,比如某些人利用信众的迷信思想骗取钱财、信众因宗祖崇拜引发坟权山权之争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信众深信天命观而放弃主观努力等。鉴于侗族民间信仰功能的两面性,各级政府既不能武断取缔民间信仰活动而伤害了民众的信仰自由,又要加强引导、适度干预,做到充分利用其正向功能为建设和谐侗区服务,又合理规避其危害社会稳定、伤害信众利益等负向功能。只有将侗族民间信仰置于国家权力的合理监控之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传统文化资源服务社会建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