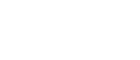归化,即在不损害原语所表达全方位信息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标准和习惯的语言形式再现这种信息。由于翻译活动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归化会受到时代及文化的影响,即在不损害原语所表达全方位信息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标准和习惯的语言背景、译者和读者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时代背景主要涉及不同时代人们对可译性的认识,不同语言、民族和文化之间共性的大小及融合程度的高低,还有不同时代的翻译观即翻译标准问题,体现的是不同时空环境中主、客观世界关系的一些特殊规约,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社会文化特征。译者因素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主观因素,译者翻译时选材是否适当、他的语言水平、背景知识、翻译标准观、文化及思维习惯等,都会影响到他译文的归化程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注意避免主观随意性,甘当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看不见”的“第三者”。读者对译文归化程度的影响体现在译者开始翻译之前及整个翻译过程中。读者是译者开始翻译时头脑中的一个假设,译者会为了他假设的读者而调整他的翻译活动。读者观主要影响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标准。下面论述影响适度归化的一些社会文化背景因素。
1.时代影响
翻译活动与人类发展史密切相关,并且总是与所处的时代相适应,一般说来,不可能进行超越时代的翻译活动,它受到时空环境的限制。
从哲学意义上说,翻译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翻译活动涉及三大要素,即人、物、场。人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物指翻译客体,即实践的对象,包括原文和译文;所谓场,则指翻译场,是翻译活动的时空环境,或称场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翻译活动不会超越物质的发展阶段,归化也是在翻译活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
首先,在一定的时代,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对翻译活动的本质与目的等的观点有局限性。它直接影响翻译的归化程度。如越是早的时候,人们越是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即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可译性大于可译性,这自然会束缚译者的手脚。如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有两位贡献很大的人,一位是释道安,一位是鸠摩罗什,他们大约同是东晋时人。释道安研究了他人的翻译并亲自参加了佛经的翻译后,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总结出翻译保存原味之难。罗什则在与他人认西方辞体时说:“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见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咏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马祖毅,1984)
翻译大师的观点尚且如此,他人更可想而知。当然,现代对翻译的认识比较客观,承认某些情况下某些语言形式不可译的同时,充分看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并给予最大限度的意义传达。
其次,在一定时代,不同语言、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共性的大小,融合程度的高低,对翻译归化的影响很大。语言的共性大,则对等词汇相对就会多一些,语法、习惯表达法相通之处也会多一些,如英、法语之间的传译相对就比英汉之间和法汉之间的传译容易些。文化因素不仅包括表达一般概念的语言因素,还包括各种超语言因素,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社会文化特征。如果两种文化比较相像,差异较少,则翻译时文化背景方面就会少一些干扰,从而有利于归化。
再者,归化程度与不同时代流行的翻译标准有关。翻译的标准问题是争论最大、时间最长,也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绝对的、人人赞成的标准。如“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马祖毅,1984);三国时的支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约,故其出经,颇从文丽”,并批评他人“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从而引起文、质两派的一场争论,质派反驳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经达。”(马祖毅,1984)
以后,唐玄奘提出了八字原则: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此外,他还制定了“五不翻”原则,这些都影响着佛经翻译的归化程度。后来严复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说,到今天还有很大影响。再往后有长时间的“硬译”、“直译”与“意译”之争,朱生豪的“神韵”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这些均主要针对文学翻译而言),更有面向一切翻译的“忠实,通顺”标准,等等,不一而足。广大译者或多或少会受到别人理论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他译文的归化程度。
2.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是翻译过程中最复杂、最难把握、最难处理的因素,这是因为文化因素过于庞杂,包罗万象;一个译者一生之中,连自己本身的文化都难以完全了解掌握,更何况还要面对另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
关于文化的概念,各门学科从不同的侧面有不同的解释,林林总总,不少于250种(戚雨村,1996)。在我国的辞书中,一般对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和组织机构,有时也特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精神,以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相区别。这样,文化的范围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次:(1)物质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制作的各种实物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建筑物、服饰、食品、用品、工具等。(2)制度、习俗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来的,包括制度、法规及相应的设施和风俗习惯等。(3)精神文化,它是通过人们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方式和产品表现出来的,既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信仰,又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和产品(王东风,章于炎,1993)。 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在一定意义上虽然也是文化知识,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不仅包括表达一般概念的语言因素,还包括各种带有非认知性质的超语言因素,它们是表明不同时空环境中主、客观世界关系的一些特殊规约,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社会文化特征。同一语言符号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脉络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语言是文化的语言,翻译是对异域文化的阐释。因此,归根结底,语言的翻译就是文化的翻译。
不同民族的文化既存在同一性又存在着差异性。同一性即文化共性,差异性即文化个性,具有地域性或世界性的文化共性总是通过民族性的文化个性反映出来的。文化翻译既要研究不同文化的共性,更要对比不同文化的个性。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进行翻译,保持原文的特长与发挥译语的优势是并行不悖的,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牺牲另一方面都会导致翻译走向极端。只有将二者完善地结合起来,才能将一种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言语的意义与内涵用另一种言语再现出来。
不同文化之间共性大,则翻译时较容易处理。如英语和汉语句子的主干基本相同,都是主、谓或主、谓、宾形式,很多情况下,较长的英语句子也能顺序译成中文。英语和汉语中还有些共同的习惯表达法,如汉语的“隔墙有耳”与英语的“Walls have ears”,“趁热打铁”与“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人多好办事”与“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英语的“Out of sight, out of mind”与汉语的“眼不见,心不烦”,“Look before you leap”与“三思而后行”,等等,大同小异,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英汉语还有很多相似的比喻和词语联想意义,如英语说:What a dull speech! He’s merely parroting what many others have said.汉语可直接译为:多么枯燥的讲话!他不过是鹦鹉学舌,重复许多人说过的话而已。英语说:He’s as sly as a fox.汉语也说:他狡猾得像个狐狸。诸如此类(邓炎昌,刘润清,1989)。
研究共性,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个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研究翻译中的文化背景的重点。这里面值得研究的方面很多,本文拟从归化过度的角度,谈谈译入语使用民族文化色彩浓厚的词语带来的问题。
中西文化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特殊性,两种文化各自具有平等的、独特的价值。所谓世界文化,无非就是这个世界上各地区、名民族文化的总和,它必须以承认世界各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翻译是不同文化互相沟通的桥梁和工具,翻译活动的具体直接对象是语言,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也是各民族文化的载体。文化首先是通过语言形式体现出来的。巴尔胡达罗夫指出:“人类的任何语言(区别于其他一切或几乎一切符号系统)都不仅能够描述已知的环境,而且也能够描述崭新的、过去没有见到过的环境,同时这种新知的、过去没有见到过的环境的数量是无限的……因此,描述新知的、陌生的环境是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少的特性,正是由于语言有这种特性,才有可能用另外一种语言的手段传达某个民族和某个国家所特有而其民族和其他国家的生活中所没有的环境。”(蔡毅,1985)这给我们在翻译中用恰当的、中性的语言形式传达异种民族文化特色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语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已经吸收了除上文提到的“科学”、“民主”、“灵感”等外,还有“卡拉OK”、“迪斯科”、“T恤衫”等外来词,以及“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新表达法,还有句子延长、主语和系词增加及可能式、被动式等欧化语法,这充分体现了汉语的包容性。
此处本文使用“恰当、中性的语言形式”的说法,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说明在翻译有异国民族特色的词语时,避免过度归化,避免抹杀异国特色,或者凭空给原作染上本国的文化色彩。这也是鲁迅当年遇到的一个难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当然,他所谓的“归化”即本文所谓过度归化。)并主张“必须有异国情调”,“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不应当“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就“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见《“题未定”草》)。
下面举例加以说明。
例1.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杨巨源《城东早春》)
The landscape which the poet loves is that of early May,
When budding greenness half concealed enwraps each willow spray.
That beautiful embroidery the days of summer yield,
Appeals to every bumpkin who takes his walks afield.
(Giles)
原诗中的“新春”,一般在公历三月左右,在译诗中变成了“五月初”(early May),而且原诗中盛春的景色,到了译文中成了“夏天”的景色(the days of summer yield)。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译者认为英国的春天不如中国的春天美,只有他们的夏天才担得此任,所以也许为了读者着想,让他们欣赏得顺利一些,就做了“置换工作”。这样做,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因为,一是它歪曲了原意,二是削弱了文化传播作用,三是若有人以此研究中国,还可能引起误解。
例2.请看《红楼梦》中两个句子的英译:
原文:(1)世人都晓神仙好。
(2)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分别是:
(1)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2)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英国人David Hawkes和John Minford的译文分别是:
(1)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2)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汉语中“神仙”、“天”等这类词都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联想意义,是汉文化中的典型词汇,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这属于不同文化中的“语义空缺”现象。笔者认为,译这类词时,不必强求一致,应以不给译文读者造成错误联想为最低条件,可以通过一些变通手段,如释译、转换、浅化文化特征,尽量保存原文风味。杨译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分别译成“immortals”和“Heaven”,原文的文化味道有所流失,但不至于给读者带去错误信息。而Hawkes的译文分别译为“salvation”和“God”,则值得商榷,因为这两个词都带有比较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除了它们与原文的意思有出入外,还可能使西方读者错误地以为中国的宗教思想与基督教相似,甚至认为中国也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这种副作用,我们在翻译中不能不尽量避免。
无独有偶,还有人主张根据词语的使用频率大小,将英语的“reaching the third base”(美国打棒球用语,意为“上了第三垒”,喻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译成中国人熟悉的麻将术语“听张了”,因为“reaching the third base”在美国是句非常普通的话,而中国人很少有人打棒球,译成“到了第三垒”则大部分将不知所云,这样译文“见次频率”不等值(王天明,1994)。但笔者认为,追求这样的等值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太可能的,随着文化交流的进行,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会越来越深,一时的“不知所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改译,可能让人“永远”不知所云;而且再想一想,让美国人嘴里说出“听张了”这种连一些对麻将不熟悉的中国人都可能感到陌生的“专业术语”,会给人滑稽感。
例3.(1)Angry as I was, as we all were, I was tempted to laugh whenever he opened his mouth. The transition from libertine to prig was so complete.(F.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尽管我和大家一样感到气愤,每次他一张口我就忍不住想笑。一个酒徒色鬼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道学先生。(何维湘,1989)
(2)La misere, cette divine maratre, fit pour ces deux jeunes gens ce que lerus meres n’avaient pu faire: elle leur apprit l’economie, le monde et la vie; elle leur donna cette grande, cette forte education qu’elle dispense a coups d’etrivieres aux grands hommes, tous malheureux dans leur enfance. (Le Cousin Pons, P.91)
贫穷这位圣明的后母,把两个青年管教好了,那是他们的母亲没有能做到的;她教他们懂得节省,懂得人世,懂得世故;她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方式给大人物(他们的童年都是艰难困苦的)受的那一套严厉的教育,也给他们受过了。(许钧,1996)
上面两段都是名家译笔,但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巫宁坤先生把“prig”译为“道学先生”,与傅雷先生的译文中出现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种汉文化色彩非常鲜明的用语,在他人的译文里并不鲜见。傅雷的译文中还出现过“杀手锏”、“中庸之道”等文化色彩较浓的词语。这样的译法倒是省了读者费心去琢磨原文文字,但既抹杀了原作的民族形象,又无端地给原作蒙上了一层中文色彩,似乎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孔孟之道都十分精通,但读者细思就会感到与原文文化氛围不协调,从而怀疑译文的真实性。这恐怕是译者所不曾想到的,更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总之,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原文中一些民族色彩较强的形象难以再现,译者或出于表达的需要,或为了易于译入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常常会对原文中一些个性较强的形象作些改造。这里就有个度的问题,笔者认为,尽量尝试用较为中性的译入语手法直接移植原文形象,从翻译的功能看,也许能起到丰富译入语的作用;从翻译的效果看,恐怕也会因原文形象的新奇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欣喜。因此,在涉及原文民族文化形象时,译者应努力保留这种形象,再三权衡,力戒随意性,避免过度归化。
3.译者因素
上面所论述的总的来说还只是翻译活动中的客观因素,是外在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观因素,内在的,就是译者因素。
译者进行翻译活动的第一步是选材。选材是否适当,是影响他能否译出归化译文的关键。我们认为,译者不应勉强去翻译他所不擅长的题材(当然,作为自己练习提高或其他特殊原因,则另当别论),如搞文学翻译的,接受专业性很强的科技材料时,就应三思而后行;而一直从事专业翻译的,也不一定能译好纯文学的东西。勉为其难,既费力,效果又没有保证。在选材上,我们应当向严复学习。贺麟在《严复的翻译》中说:“严氏所选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凡与原书有关系的书,他都涉猎过的……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通观翻译史上,关于选择原书一层,处处顾到,如象严复的,实未之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进行翻译,除了一些本来就不可译的因素外,只要有责任心,则应能保证译出好文章。 第二步是对原作进行分析理解,这里体现译者的外语能力。但是单纯外语水平高的人,不一定就能译出好文章,一定要经过翻译训练和相当时间的翻译实践锻炼,才可能做到得心应手。除了外语能力,分析理解原文还需要译者的知识十分丰富,也就是说,除了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有渊博的背景知识,这是上述复杂的文化因素决定的,也是为什么吕叔湘先生呼吁广大翻译工作者要成为“杂家”的原因。
第三步是译语表达。这里要求译者有高超的母语水平。正确理解了原文后,母语词汇贫乏、语法不清、不懂修辞、分不清语体、文体混乱,则译不出归化的语言。因此,好的译者双语水平都要好。但是,双语都很好的人,有时也难免译出不合译入语习惯的作品,这就提出了另一个必要条件,即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语法、习惯表达法的比较;通过对两种语言进行对照、比较、辨异,才能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才能做到将两种文字融会贯通,做到运用自如。
另外还牵涉译者的翻译标准观问题。前文讲过,迄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标准”,每个译者自己心里都有一杆秤。他这杆秤向原作偏一点,是一种效果,向译作偏一点,就又是一种情况,最难的是找准平衡点。主张“直译”的人,则“宁信而不顺”,而主张“意译”的人,走向另一个极端――“顺而不信”。还有人主张“翻译超越论”,主张“发挥译入语优势”;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翻译出来的译文,往往容易出现擅自增删、美化、优化、雅化原作的情况,而信息失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片面的标准观不可取。本文所提倡的归化标准,要求译者照顾着两个方面:译语符合标准、习惯的前提是真实传达原文的全方位信息。
关于译者主观性对归化程度的影响,还可以用译者“先结构”的概念进行分析。什么是“先结构”呢?简单说就是由于人的一切活动都必然受着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人们理解任何事物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以其固有的意识去积极地参预。按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以我们意识中的“先结构”去参预。翻译的过程首先是译者接受“本文”信息的过程。但是译者绝不是被动地接受。他通晓出发语言及归宿语言,并掌握了其一定的文化历史结构,因而他一定程度上既是原语读者又是译语读者。但除此之外,他还更有自己的立场、观点、趣味和风格,也就是他的“主观性”。这三个因素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译者独特的先结构。不管译者是否意识到,是否承认它,这种先结构总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十分活跃。一般说来,这种先结构可能有三种状态:(1)先结构低劣。在这种状态下,译者同原作几乎格格不入,既不能理解原作,又不能再现原作,无法达到平衡。硬着头皮去译,结果可想而知。(2)先结构过强而又无法抑制。在世界翻译史里,有过这种状态的译者也不鲜见,如《鲁拜集》的译作者菲茨杰拉德,以及“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的林纾林琴南,还有主张“翻译超越论”者,等等。这类译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动手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或者依据自己的趣味和标准,大刀阔斧地对原作进行重新排列组合。这类作品,其实最好叫“改译”或“编译”,已难称一般意义上的翻译了。(3)先结构与原作者相当。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可以最终达到平衡的结构(袁伟,1987)。那么从归化的角度来看,先结构低劣者,其译文一定是归化不足的;先结构过强而又无法抑制者,其译文通常是归化过度的;先结构与原作者相当者,才能译得恰到好处。
总之,译者的因素复杂而且不像语言因素可以总结规律,它没有固定的标准规范。这种主观性影响的恰当与否,完全取决于译者本人素质的高低。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最低可遵守的原则或建议,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注意跳出自己,避免主观随意性,努力做好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看不见”的“第三者”。如果译者能做到这些,则归化有望。
4.读者因素
凡翻译活动必有其接受方,即读者(本文此处的读者概念不包括译者自己,因为有些人翻译是为了自己欣赏或自己保存资料,则不在此列)。读者也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之一,读者因素对翻译产品最终状况的影响不可忽视。
每个译者在开始翻译活动时,头脑里通常者已有了一个预设的译文读者,这个想象的读者对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标准和原则,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严复当年译《天演论》、《法意》等书时为什么选择用文言文来译?除了他认为“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外,还有重要原因是“欲力求旧文人看懂,不能多造新词,使人费解”(贺麟:《严复的翻译》),这是较早的读者观,也是他“信、达、雅”三原则中“雅”字的由来。
鲁迅在谈到翻译原则时,认为不能抽象地谈,于是提出了划分读者层次的观点。他在给瞿秋白关于翻译的回信里说:“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我还以为即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鲁迅主张“直译”,原因在此。
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说:“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译莎事业,只为了“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
美国的奈达主张,翻译的第一任务,是使读者看了译文就能一目了然。所以赞成把古代见面打招呼时的“神圣地亲亲嘴”译成现代的“非常热情地握握手”,这是他读者接受论的基础。
总之,翻译活动中,读者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我们的归化原则中要求译语符合“标准和习惯”,就是读者观的体现。为读者着想,就要努力做到译文留洋味,去洋腔。 总之,翻译活动本身复杂,连带它的“副产品”――错误也很复杂,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前文论述了影响归化的各个非语言方面,就是为了说明如何把握好翻译中归化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