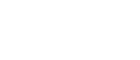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15-03
引论
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华帝国被动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以入侵者和先进文明的传播者的双重角色刺激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催化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国市民社会在清末民初这个内忧外患、矛盾纷繁复杂的特殊时期尴尬萌芽。如果按照阿尔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1963)中比照美国价值标准对中国文化变量计算等级,无疑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基因是先天不足的。而狄百瑞摈弃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的诱惑,积极肯定了中国市民社会萌芽的意义。他认为,中国清朝末年存在一个即使不完全相同但也颇为类似于早期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1]。遗憾的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举步维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虽然实现了新的社会整合,但是却以建立超级官僚系统的社会为代价,全能主义政治吞食了近代以来不断萎缩的民间社会。随着全面危机的消退,全能主义政治的负面作用逐渐暴露出来,用吞没民间社会的办法实现社会整合的效度下降,社会呼唤国家之外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现代化发展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解放思想,开始了探索计划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中国开始羞答答地进行市场经济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正式肯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随后中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的自由发展为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奠定了物质基础,国家在财产关系、社会生活等领域为人们留出更多自主空间,以契约为基础的个人权利得到尊重。经济的现代化是市民社会成长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经济现代化有力地带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作为市民社会核心要素的非营利组织和形式各样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按照查尔斯?泰勒对市民社会最低限度的定义,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产生[2],那么中国已经迈进市民社会阶段;但是如果按照查尔斯?泰勒对市民社会较为严格的定义,中国还算不上存在独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①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或经济现代化是市民社会成长的硬件设置,那么公民文化或文化现代化就是市民社会必需的软件配置。就我国而言,经济现代化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文化现代化明显滞后于经济的现代化,我国市民社会发展因此囿于文化的滞后而步履蹒跚。
一、我国市民社会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首次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1956)。在他看来,大传统是城市中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小传统指乡村中大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传统被解释成社会文明,小传统仅是民俗文化;大传统创造文化,小传统只能简单地接受文化。继雷氏之后,吉登斯把“大传统”视为书面文化,包括宗教、民族国家的规范意识形态等;“小传统”指口承文化,包括魔术、巫术、习惯和日常生活惯例等[3]。虽然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有值得商榷之处,学者们对“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解也各有千秋,但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视角给曾经长期分裂的文化单向度解释以有力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融合复杂,“大传统与小传统”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分析工具,对中国市民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析有着积极意义。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文化主要是社会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所掌控的,“小传统”文化主要是社会中下层农民所持有的文化。笔者在修正的基础上借用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小传统”概念。为了对中国市民社会传统文化分析的广涵性,笔者分别扩大了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大传统”文化是指与国家和权力紧密相关的、社会中少数上层和知识分子所掌控的文化;“小传统”文化是社会大众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它向社会所有阶层开放。由于学校教育的精英性质,“大传统”并不向社会中下层阶层渗透;而“小传统”的普遍渗透力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强大的惰性使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一)“主动调试”的“大传统”
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存在着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流派争奇斗艳,但就其影响力、渗透力而言,中国“大传统”的主流是基本稳定的。林毓生用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捆绑的模式分析中国“超稳定结构”的宏观模型也肯定了意识形态(“大传统”)的恒常性。由于中国“大传统”与政治制度的相互依存关系,自封建社会至今中国有两个最重要的“大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的传统是有自我调适能力的传统,当然这种自我调适需要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的解释来完成。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虽有“民贵君轻”、“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但是没有市民社会意义上的“民主”思想;虽有强调“臣民美德”的义务观念,但没有有关“公民权利”的修辞词汇;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私和公的界定,但是“修齐”和“治平”是一以贯之,连带性的公模糊了公私的严格界限。总之,传统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显然并不支持市民社会的发展。然而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在西方的冲击下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程,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使儒家思想渐渐失去了立足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全面反传统主义的高潮,“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在近代知识分子的倡导下有力地冲击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儒家思想的制度化之路也就此终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余英时等几代新儒家思想家重新挖掘儒家思想的精粹,他们一方面对中国传统做新的诠释及应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同中国传统智慧融会贯通。他们既不回避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危机,又通过新的阐释使传统思想获得新生。如,余英时坦然承认儒学面临的困境,他曾把现代儒学比喻成“游魂”。但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特征使价值之源没有实质化、形式化,没有西方由上帝观念而衍生出来的一整套精神负担,反而使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在不会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基础上对科学采取开放的态度[4]。虽然新儒家低估了儒家思想对社会历史的负面影响,甚至带有纯理论的色彩,但是它反映了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大传统”开始以开放的态度应对市民社会的挑战,它试图主动与市民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接洽。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再次与政治结构融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传统”,因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必然成为中国当代市民社会发展的理论资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时期,它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色彩。他一方面肯定市民社会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他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了市民社会的弊端,从人类解放的高度历史性地否定“利己主义”、“异化”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逻辑上的批判否定是以建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为归依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解读或误读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排斥加上全能主义政治对市民社会的吞食,使市民社会在中国缺乏生长的政治文化土壤。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权之外的公共领域开始产生。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实践增强了对理论支持的迫切性。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反对从教条和僵化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知识分子深入文本深化了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认识。有学者发现马克思虽然强调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但是其理论具有“破中有立”、“以破求立”的理论特征,“破”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立”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唯物史观的建构与阐发[5]。学者们发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本身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早期的作品中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在后期作品中他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从与一切生产力相关的物质生产关系层面上阐释的。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读既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资源,又警惕人们市民社会的弊端,建设社会主义特色的市民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市民社会理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实践土壤上的有机养分。
(二)“保守倔强”的“小传统”
如果说“大传统”是制度层面的文化形态,那么“小传统”就是非制度的、习惯性的存在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隐性而潜移默化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模式。中国的“小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成熟而异常发达的农业社会使中国的“小传统”拥有浓厚的“乡土情结”。面对市民社会的新语境,与中国“大传统”的式微和主动调试相比较,“小传统”体现了变迁的惰性和异常强大的生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似有与市民社会理性化的契约观“格格不入”之嫌。
韦伯用“理性化”描述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和特征。韦伯的“理性化”源于其“社会行动”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人的行动有四种类型,即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传统行为和情感行为。他用理性人预设了人类行为遵循的原则,因此工具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被认为是更重要的,以非理性为特征的传统行为和情感行为在韦伯的理论中被边缘化。西方的市民社会是以反传统的“理性主义”为特征,而中国“小传统”的生活话语是伦理秩序。那么中国的伦理秩序是否是反理性的呢?我们仍然可以从韦伯对“理性化”概念的分析中找到答案。韦伯的“工具理性”强调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需要考虑采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手段;“价值理性”是用合理的方法去追求那些我们认为是合理的价值。从“价值理性”的观点,真诚、友善等价值观是理性的,有其自身存在的理性价值。但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而言,二者并不一定是正比例关系。“工具理性”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价值理性”的萎缩,“价值理性”的复兴又会限制“工具理性”的应用范围。西方市民社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发展同样展现了二者的不平衡性。大体而言,“工具理性”为西方市民社会带来了高效的生活,西方市民社会的理性特征更多体现为“工具理性”。
从表面上看,中国民间“小传统”确实存在大量与西方市民社会“工具理性”不同的因素。一方面,“小传统”用礼治对抗法治。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治社会,宗法是以血缘为基础的遵循“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行为规范。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性中国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7]。人们对礼的主动服膺来源于经过教化的对违反礼而产生的内心畏惧感。乡土性的礼治社会是排斥法治和诉讼的,法治社会的诉讼被认为是挑拨是非。另一方面,“小传统”用家庭或家族对抗正式组织。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社会人伦关系的差序性特征,私人关系、人情哲学是以家庭为基础扩展至整个家族,私人领域的人情原则与公共领域的行为规范具有连带性的关系。中国“小传统”中公私的模糊性与以契约为基础的正式组织中公私分明的团体道德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小传统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保守顽固”的角色,但是它并非绝对排斥市民社会的发展,而是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推进市民社会的发展。无讼的礼治社会用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取代正式的法律法规,起到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缓和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初级组织的行为原则渗透正式组织中,从而使正式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具有连带性特征,这有利于社会互助合作和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中国的民间“小传统”并不否定人的物质需求,但又并非以功利目标为最终归依;它虽与感性有着某种关系,但又不同于感性;它虽没有正式规范,但却能调控人的行为,实现某种和谐、共赢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民间“小传统”与“价值理性”存在相似的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价值理性”的原则。
二、余论
中国学界对市民社会的文化探讨存在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仅是“大传统”或者“大传统”可以概括“小传统”,因而忽视了“小传统”的存在;另一种认为,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民间“小传统”是历史的残存,市民社会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应致力于新的制度化取代民间“小传统”。然而中国“大传统”和“小传统”变迁的形态和模式显然是不一致的,忽视甚至全面否定“小传统”更是不足取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无需用西方的价值观取代中国的文化传统,更不能打着“科学”、“民主”的假信仰代替真信仰。正如林毓生所言,“把另一种文化的一些东西当作口号是相当简单的,但口号式的了解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当可怕的口号变成权威,就会产生‘形式主义的谬误’。”[8] 面对市民社会的新环境,与“大传统”的主动调试相比较,“小传统”更多表现出变迁的惰性。虽然“小传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适应和推进市民社会的发展,但是不可否定这种效力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中国“小传统”发挥效力是以相对稳定的封闭的乡土社会为前提,环境的稳定为传统的有效性提供了基本保障。然而全球化、现代化的市民社会是快速变迁的社会,开放的环境必然使传统失效,需要用契约的形式规范人们的行为。中国市民社会文化之路需要既抛弃西方中心主义,又否定世界体系理论,在二者融合中找到适合中国的道路。一方面,促使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转化,在社会不被破坏,文化传统保留的基础上寻求市民社会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衔接。中国民间“小传统”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与“大传统”的沟通明显不足,我们需要打通社会上层对大传统的垄断,变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以促进大小传统良好互动来推动传统文化的内在转化。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是几千年的民族积淀的结果,生命根基的深厚使其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转化,需要脚踏实地地稳步前进,或许林毓生先生的“比慢”精神恰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