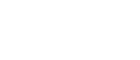一、两个领域的集中――“十七年”时期
(1949―1966)的电影传播模式新中国诞生的头“十七年”里的电影传播是在接受与试图否定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展开的。这一时期的电影传播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首先是生产管理高度集中的编码过程。当时的电影活动被纳入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广泛的影响力。由于影片的符码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尽管不总指涉现实生活,但是电影却是只需要调动基本的视听感知就能完成“阅读”的一门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具有特别广泛的群众基础,“根据苏联管理电影的经验,中国的领导者意识到,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还是最普及的娱乐方式,无论在大中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影响广泛,因此被用作最得力的宣传工具”[1]。
第二,复杂的工艺。当时的电影毕竟还是一种需要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文艺形式,“一种与工业、科技密切相关的特殊产品,而产品则是要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范围的”[2]。
而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当时的影片的传播是通过以下的方式进行的:在影片传播的生产阶段由“电影局统一进行题材规划,各电影厂承接具体拍摄任务”;影片传播的销售阶段,“电影发行由电影局统购统销,配合宣传需要和城市乡村的不同特点安排影片上映”,从而形成了“生产与营销管理高度集中”[3]的局面。胡菊斌曾形象地将1949年到1976年间的国营电影制片厂比喻为“加工工厂”,即“生产计划、题材比例、剧本选择基本上都是由电影局一手包办的,甚至摄制组也不是自愿组合的,摄制影片的生产组织不是以导演为中心,而是以行政领导者为中心。各国营电影制片厂的职责就是保证按照上级――电影局的规划完成任务”[4]7。以剧本创作活动为例,其具体过程是这样展开的:先是由电影局艺术处将所有编剧分成“东北(驻沈阳)、华东(驻上海)、西北(驻西安)、华北(驻北京)和‘部队’等五个小组”,然后,除了留守的以外,“外出编剧同志,大多接受领导上分配的主题和任务期限,就地体验生活取材创作”[5]。接下来编剧们再创作好之后的活动,在1956年以前是由电影局统一将创作好的剧本分配至下属的各制片厂进行摄制,在1956年以后是由各个电影制片厂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本厂的题材规划的制定,而电影局负责各个电影制片厂的统筹和平衡以及总方针的制定,不再负责剧本的组织。[4]32这是因为,电影局曾于1956年10月26日至11月24日召开了全国制片厂厂长会议,即著名的“舍饭寺会议”。会议决定对以苏联模式为参照建立起来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进行重大的改革,提出了以“自选题材”“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和“导演中心制”为主要内容的“三自一中心”的改革方案。[6]会议之后,文化部开始对电影厂的管理体制进行了下放,只是从宏观上保有对生产总量与具体分配的控制。[7]但是,由于接踵而至的“反右”斗争的不断冲击,而且“下放”过程本身也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8]致使期望摆脱“苏联模式”的良好初衷根本没有条件实现。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这种“下放”并不是体制的变革,并没有把电影的生产与销售交付给市场,而是转移给了地方行政机构进行领导,将电影的生产过程纳入地方的文化工业生产序列,因此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计划经济下的高度集中管理的局面,只是一种管理上的重新分配,“这些做法纯粹是由于一定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因而对于改变僵化的电影体制始终未有裨益”[4]17。发行与放映阶段的“集中性”真正得以完全体现的是在1963年2月,国务院以125号文件转批了文化部《关于改进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管理体制的试行方案》。该《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各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经济分配形式,即电影节目由中影公司统一向制片部门收购,拷贝统一由中影公司安排洗印、分配和调度”[9]。这种依照苏联的经验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于整个电影系统的管理不仅仅是“从制作到发行放映,还包括电影的宣传、教育、出版、研究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10]186。也就是说,被视作“讯息”的影片的传播被高度集中的手段管理了起来,而且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已经渗透到了这种“讯息”传播的各个环节。除了国内的影片传播之外,国际的影片传播交流也体现出一种“集中性”,即以意识形态的亲近性和认同度为依据进行有计划的影片输入与输出。[11]比较鲜明的体现是原本受热捧的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影片随着意识形态的分歧而逐渐从我国银幕上消失。总的来说,这一切即形成了夏衍所描述的局面:“影片的主要生产数量和质量跟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很直接的关系,而且电影是首当其冲的。”[12]
其次是思想意识高度统一的解码过程。采用拉斯维尔的线性传播模式来进行研究利弊鲜明:该模式明确阐释了传播活动是“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但是却“没有揭示人类社会传播的双向和互动性质”[13]。有趣的是,拉斯维尔的线性传播模式的这一特点恰好概括了“十七年”时期电影传播的特征 。因为平等是交流的前提。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传播的过程中,受传者一方与传播者一方的交流并不处于平等地位,受传者并不能由于表达了基于影片传播效果的反馈而获得成为这一传播格局中具有“自主性”身份的地位,这正是这一时期电影传播格局中受众的普遍特征――缺少表达反馈的条件,只能在有限的传播空间内表达诉求,即无法在电影制作者(编码者)和电影观众(受众)之间搭起桥梁,“不能适时有效地作用于电影工作的实际”[14];还有一点,特别是在“十七年”时期,受传者所能表达的有限的“回馈”还受到了“噪音”的强力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由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所体现的“出于特定政治目的对电影文本进行定向读解,可以为形象赋予某种政治含义,再对这种意义确定政治性质,展开政治批判”[10]191以及自此以后发生的一系列的用政治话语来统领大众对于艺术作品反馈的事件。因此,政治话语的强势影响使得解码者的二次编码行为不得不附和于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而原本能促进电影向前发展的“健康”声音也逐渐消弭,先前有的能够与原始编码者所进行的能动的、充分有效的、良性的互动或是反馈越来越不能够成为原始编码者们继续创作的参考和对照,而指令的策源地成了政治话语,最终导致了单向度的传播渠道的形成,这也正是为什么拉斯维尔的线性传播模式能够用来概括这一时期传播特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缺乏对于效果的回馈,而是缺乏对于效果的有效回馈,在传播循环的回路上架起了一条似有似无的“虚线”。这便是“十七年”时期的电影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治化的文本解码的强大威力。而这一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直至“文革”的爆发而走向极端。 二、两组关系的互动――“十七年”时期
(1949―1966)的电影传播机制在厘清了“十七年”时期(1949―1966)电影传播的模式和特征之后,这些元素是如何相互作用而构成了一个系统?这一系统又是如何运作进而影响电影传播的呢?这是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电影传播格局主要是通过几组关系的互动来运作的。首先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这一时期电影传播格局的一个鲜明方面是,主动的政治指令与自觉的创作冲动之间的角逐与对话。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待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于电影文本的编码所带来的影响。由于电影生产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这一过程就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将电影生产活动纳入统一的体制当中进行管理,就可以使得电影的制作有充分的物质保障。“那时,只要剧本被通过,拍摄经费是不成问题的;创作人员的生活就有保证;”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也无需为影片发行情况不好而伤脑筋”[2]。这种情况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弊端:由于电影创作者自发的艺术创作受到了体制的限制,进行电影创作活动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令。在剧本创作方面是“上级命令,下级服从”,在生产组合方面是“强迫结婚,少数服从多数”,在发行放映方面是“只此一家,没有竞赛”[15]。
其次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这一时期电影传播格局的另一个方面是,政治话语与艺术表达之间的角逐与对话。这一组互动关系的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对艺术作品进行编码的时候,试图用艺术手段图解政治话语;在对艺术作品进行解码的时候,试图通过对于形象的功利性读解来服务政治斗争。
从编码阶段政治话语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对话来看,起初,政治话语介入文本传播的过程之中是为了保证作品的思想性,但是,这一介入活动逐渐发展成为片面强调电影在进行大众传播时所具有的强大宣传效果,忽视了影片本身作为一件艺术产品所具有的艺术属性,进而可能导致传播效果被削弱。这样一来,“尽管主题思想是像政论一样的正确,动机也是善良的,可是政论不能代替艺术,在艺术欣赏上,不可能要求人们服从于‘有啥看啥’,人们可以保留选择的权利,完全有权利不爱看概念化公式化教条主义的影片”[16]。
而在对影片文本进行解码的阶段,政治与艺术的对话的局面产生了两种类型的影响:一种是对于一般的自发的观影观众而言,由于政治内容不断地在银幕上进行渲染,导致了“人们养成了奇特的观影方式:一种负载着强烈政治色彩的身心愉悦,将看电影视为另一种体验政治激情的活动,并自觉地认同其政治内涵,认作另一个思想教育的课堂”[17]。另一种是对于自觉的影片解码者而言,其针对影片本身的读解活动越来越靠向政治阐释,不仅仅表现在电影活动逐渐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起点,而且政治话语不断地介入这一过程当中,通过对影片采取过度地诠释和臆造或出于一定政治目的的读解隐喻含义等手段来为政治需要服务。另外一点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这种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对话格局,即前文所说的以意识形态的认同为依据的影片输入,尽管其中的部分影片确实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但是海外影片的传入首先还是要跨越政治许可的“门槛儿”。
无论是从宏观的传播模式来看,还是具体审视单个的传播文本,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电影传播局面的形成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艺术创作的个性需要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电影的传播场域进行了一次次“短兵相接”之后不断“落败”的过程。在二者不断角力的过程中,艺术创作的自由空间越发狭小,最终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展开与政治话语的周旋和妥协,即在“泛政治化”的背景下适当削弱宣教功能,努力保留影片的通俗、愉悦的成分。[17]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新政权成立时期特殊的环境,导致了电影传播的格局必须服从国家政令的统一调拨,而这一因素恰恰又能为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尽管影片是以“生产―供应―销售”的流程进行的传播,但是电影事业的发展仍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局面,并且给予了国家经济有力的回馈,[18]从而形成了一个有计划的、高度集中的,以政治标准为中心和准绳的电影传播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