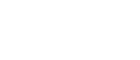关键字:现代性 先锋主义 文化语境
【内容提要】先锋主义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颜面之一。先锋主义是有着自觉的先锋意识与行动并有社会文化观念相匹配的群体审美思潮或运动,至少需要三个要素:一是自觉的目的明确的群体行动,二是艺术形式的激进实验,三是与形式实验相匹配的美学观念与社会文化观念。中国的先锋主义具有明显的晚生早衰性。随着既极端先锋而又极端反先锋的后现代思潮兴起,先锋主义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或成为文化消费时代文化商品的一种商业包装。先锋主义的晚生早衰特性乃至它的没落,都与特定文化语境的特殊需要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曾经兴起一股以“朦胧诗”、“后朦胧诗”、“先锋小说”等为标志的先锋文学潮流,它以强劲的反叛与建构意识席卷文坛,既在反叛中建构、又在建构中反叛,迅捷地演变成90年代严肃文学的新主流。如今,当这种先锋潮流在消费文化的洪流中已呈落花流水态势时,回头对它加以审视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传统及未来。本文即是从现代性的颜面这一视角去考察中国先锋主义的一次尝试。
一、现代性的颜面
先锋主义难道也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颜面之一?“现代性的颜面”(faces of modernity)是美国学者马太·卡林奈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副颜面》(Five Faces of Modernity,1987)中提出来的问题。“现代性的颜面”应是有关现代性的审美艺术表现、或审美现代性的具体呈现面貌的一个隐喻性表述,不妨视为考察现代性的一条有用的思路。我在这里用汉语的“颜面”而不是通常的“面孔”一词去翻译英文face,是想尽力贴近审美现代性所与之不可分离的颜色、形体、声音等艺术形式特征。颜面,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中国京剧中多采多姿的“脸谱”,它决不只是固定不变的或唯一的,而是可以时常涂抹的和变换的,在不同场合亮出不同的风韵。卡林奈斯库的这部著作以西方现代艺术为根据,勾勒出现代性在审美表现上的五种颜面:现代主义、先锋主义、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他主要考虑的是“审美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的具体表现形态问题:“把现代性、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放在一起的最终原因是美学上的。只有从这种美学视角看,这些概念才显露出它们更微妙、更费解的相互联系”(注:[美]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Modernism,Avant-Garde,Decadence,Kitsch and Postmodern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8.译文采自马太·卡林奈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16页。)。他认识到,审美现代性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即从一种由来已久的永恒性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性与内在性美学,前者是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的理想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和新奇”(注:[美]卡林奈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页。)。卡林奈斯库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的颜面问题。
我关心的是,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看,中国现代艺术中哪些因素可以获得其必要的意义?我不想直接套用卡林奈斯库的“五副颜面”说,而是宁愿在沿用“现代性的颜面”说并参照“五副颜面”说的同时,主要从中国现代性语境出发,着力寻找那些能够呈现中国现代性的具体状况及其微妙方面的审美现代性因素。也就是说,在现代性颜面名义下,我将集中寻觅并展示现代艺术中专属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那些特定因素。我的做法是在历时态和共时态相结合的意义上寻找到属于中国现代性的那些特有的颜面。这样,我的脑海里渐次浮现出这样几副颜面:革命主义、先锋主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等。这里仅对其中的先锋主义作初步讨论。
二、先锋主义与现代性
提起“先锋”,人们自然会想到在战斗最前沿冲锋陷阵的士兵。在审美现代性领域,先锋派,或称先锋主义,来源于法文Avant-Garde,它最早本是军事用语,后来逐渐地进入政治与美学领域(注:有关先锋派在西方的发展与演变线索,详见[美]卡林奈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3-159页。)。在美学领域,先锋主义往往是指那种超出常规的激进的形式实验及由此而导致的观念历险、冒犯或反叛。先锋主义与现代性有什么关系?应当说,先锋主义是现代性的伴随物;离开现代性就无所谓先锋主义。善于求新求变求异的现代性,总是以先锋主义为自己杀开一条血路。不过,这条按现代性指令开辟的血路有时可能通向现代性,有时则可能反过来纠缠或抵抗它,甚至锋芒直指它本身。这样,先锋主义既可能是现代性的,是它的想象或美化的形式;也可能是反现代性的,是它的批判、质疑或自反形式。按卡林奈斯库的看法,先锋主义是与现代性不同而有密切关涉的概念。它常常“暗含或预见于现代性概念的较广范围内”,并且“在每一个方面都较现代性更激进。”这种激进就表现在,“先锋派实际上从现代传统中借鉴了它的所有要素,但同时将它们加以扩大、夸张,将它们置于最出人意料的语境中,往往使它们变得几乎面目全非。”(注: [美]卡林奈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5-106页。)显然,先锋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性的一种扩大、夸张、变异及更激进的自反状况。先锋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审美表现形式,但却是它的一种激进的变异的或者自反的形式。因而要了解现代性的究竟,不妨看看它的激进的变异形式——先锋主义;而要理解先锋主义的究竟,也需要追溯它的现代性源头活水。
在探讨先锋主义之前,有必要就先锋主义概念的内涵略加界说,因为只要这样做,才可能消除可能的误解。我以为,首先需要把先锋主义与先锋精神区别开来。先锋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激进的、变异的或自反的审美形式,应是指有着自觉的先锋意识与行动并有社会文化观念相匹配的群体审美思潮或运动。这样理解的先锋主义,至少需要三个要素:第一,自觉的目的明确的群体行动,即先锋主义应是由一个或多个群体自觉发动并引发社会激荡的行动。光有单个人的行动而缺少他人响应和社会反响,不能算先锋主义或先锋派;第二,艺术形式的激进实验,即先锋主义应具体落实为前所未有或标新立异的语言、色彩、形体或声音等形式变革;第三,与形式实验相匹配的美学观念与社会文化观念,即先锋主义的形式实验只不过是理想的社会文化形态的预演,或者说正是要为社会文化变革提供审美模型。我觉得这是任何先锋主义的三要素,缺一不可。而先锋精神,则是指只具备后两个要素即艺术形式实验及相匹配的美学与社会文化观念的状况。对于判断是否先锋主义,第一个要素十分关键。在它缺席情形下的先锋,就只具有一定的先锋精神而不足以成为先锋主义或先锋派了。
三、中国先锋主义的晚生早衰性
应当看到,先锋主义(Avant-Garde)尽管被卡林奈斯库视为西方现代性的主要颜面之一,但在中国却具有颇为不同的特殊境遇和具体表现。就我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早期和中期乃至更晚,中国的艺术家们虽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像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那样“拿来”西方的种种“主义”,但却很少提及或使用“先锋”(或其他译名如“前卫”)一词。他们可能采用先锋主义的某些具体思想或主张,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文艺行动上可能已经完全称得上货真价实的先锋主义者了,但却并没有自觉或明确地竖起先锋主义旗号。取而代之,他们索性把自己的先锋行为统合到其他主义、尤其是声势浩大的革命主义之中。中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何以没有真正自觉的先锋主义?这一点确实值得深思。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其中有两方面应必不可少:西方的先锋派状况与中国的特殊语境需要。一方面,作为影响源头的西方先锋派本身的高峰期,与中国知识分子前往取经的时间形成错位,从而导致先锋派在中国未能及时赢得发展良机。按卡林奈斯库的精细梳理,西方先锋派虽然可以一直上溯到19世纪中后期的波德莱尔(1821-1867),但却是在几乎百年后即二战后的50、60年代才达到高潮的:“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先锋派的内在矛盾是波德莱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即已预言性地觉察到的,但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它才成为一场较广泛理智争论的焦点。二战后,与这种论争的出现同时发生的是,先锋派艺术出乎意料地在公众中取得广泛的成功,先锋派的概念本身也相应地变成一个被广泛使用(和滥用)的广告标语。长期以来先锋派有限的生命完全是靠触犯众怒而获得的,转眼间它却变成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神话之一。它的唐突冒犯和出言不逊现在只是被认为有趣,它启示般的呼号则变成了惬意而无害的陈词滥调。有讽刺意味的是,先锋派发现自己在一种出乎意外的巨大成功中走向失败。这种情形促使一些艺术家和批评家不仅去质疑先锋派的历史作用,而且去质疑这一概念本身的合理性。”(注:[美]卡林奈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0-131页。)按卡林内斯库的看法,先锋派历来是依靠其标新立异的形式实验和“触犯众怒”的越轨的艺术行为而引人注目的,但只是到了二战以后的特殊文化语境中,它才突然间成为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文化神话”,而这种“文化神话”的成败祸福却是相互依存的。如果这一梳理是合理的,那么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在20世纪上半叶寻梦欧美的,未能与后来才志得意满的先锋派相遇;而等到先锋派走向登峰造极的“文化神话”的巅峰时(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早已紧紧关闭通向欧美的文化大门,关起门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直到“三突出”、“高大全”等“文革”文艺美学原则的诞生。这样,前往西方取经的中国艺术家与西方先锋派的高峰期在时间上错位了,这是中国先锋派晚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先锋派或先锋主义之晚生实出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革命主义潮流一度掩盖其他潮流的光芒的缘故。由于中国现代性的艰难、缓慢和曲折,知识分子急切地要以“革命”的非常手段去推演现代性启蒙工程,因而当革命主义尤其是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最激动人心的社会乌托邦时,先锋主义这类主要停留于形式的离经叛道之举就必然地退居次要地步了。在《新青年》杂志所翻译的外国小说中,俄国小说何以在数量上占第一位、高达39%?这种特殊关注正与翻译者的引进目的相关:“俄国的国情与中国相似,而俄国的小说在反映社会上尤为出色。”(注: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2-73页。)瞿秋白在1920年3月写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指出:“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是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都集中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注: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北京新中国杂志社,1920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激发起中国人的巨大热情和非凡想象力: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民族也能通过“掀天动地”的“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而实现民族的复兴!正由于这种革命主义想象,因而俄罗斯文学自然就成为《新青年》大力推介的外国文学范本了。显然,革命主义的辉煌动人的现实图景及乌托邦畅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因而先锋主义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慧眼中变得模糊或暗淡了,失去了可能有的超常诱惑力。由此似乎可以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大半时段,如日中天的革命主义使得包括先锋主义在内的其他一切主义都相形见绌、黯然无光、甚或偃旗息鼓。与此相连,一个看来离奇然而又可理解的情形是:先锋主义早已经静悄悄地溜进中国,甚至可能已经掀起一点儿浪花,但却不曾竖立起明确的先锋旗号。无论是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王国维的“美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还是胡适的《尝试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都体现了或多或少的先锋主义特点,如追求文艺形式的新实验及相应的文艺观念的变革。缘由何在?当革命主义成为他们中许多人的最大兴奋点、革命派远比先锋主义激动人心时,何须改打先锋旗帜?
在上述两方面的合力挤压下,中国的先锋主义必然遭遇与在西方不同的命运。这样,它的晚生性特点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而与晚生相应,中国先锋主义的早衰也是必然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西方的先锋派已经无可挽回地溃退、更无法继续向中国提供先锋必需的文化资源或“后勤保障”时,中国的突然崛起的先锋派必然会在迅速丧失战斗力后骤然归于烟消云散。因此,与西方先锋主义相比,中国的先锋主义具有明显的晚生早衰性。这就是说,中国的先锋主义是按自身文化语境的需要而晚生与早衰的。当我们考察先锋主义时,应当明确这种与西方同类并不相同的独特特点。
四、先锋主义的呈现
尽管自觉的先锋主义晚生而又早衰,但毕竟来过了。这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一是“先锋”术语的明确使用,二是“先锋主义”的实际运行。
“先锋”一词是在1980年代初起逐渐地登场亮相的。根据有关资料及研究 (注: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3页。),诗人徐敬亚于1981年在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里自觉地用“先锋”一词去描述“朦胧诗”,认为“他们的主题基调与目前整个文坛最先锋的艺术是基本吻合的”(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辽宁师范学院校刊《新叶》1982年第8期,删改稿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这里的“先锋”明显地是指在文坛最前沿冲锋陷阵的开拓者。这可能是1980年代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先锋”话语。诗人骆一禾至迟在1984年写下以《先锋》为题的诗歌:“世界说需要燃烧/他燃烧着/象导火的绒绳/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当然不会有/凤凰的再生……//当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就是长空下/最后一场雪……/明日里/就有那大树长青/母亲般夏日的雨声//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注:老木编选《新诗潮诗集》(下),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之一,1985年内部发行。)这里依次用“导火的绒绳”和“长空下最后一场雪”两个比喻来礼赞“先锋”,表露出对“先锋”的自我牺牲精神、原创作用和影响力的清晰认识,以及甘愿充当“先锋”的姿态。到了1980年代后期,“先锋”一词就逐渐地风行于文学界,产生了“先锋诗歌”、“先锋小说”等用法。与文学界乐于称道“先锋”不同,美术界则更喜欢用“前卫”一词翻译Avant-Garde,所以常见到“前卫美术”的习惯用法。
中国的自觉的先锋派或先锋主义浪潮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年逐渐地兴起的。“文革”结束后,当着长期盛行的革命主义渐次地走向边缘时,先锋意识开始觉醒。1978年12月出现的《今天》文学杂志及随之而勃兴的“朦胧诗”浪潮、1979年北京的“星星美展”及首都机场女子裸体壁画风波、1982年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实验戏剧’,《绝对信号》和《车站》等,可以说传达出先锋主义艺术思潮的初澜。随着1985年中国进入更加开放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时段以及相应的文化变革思想趋于活跃,自觉的先锋主义在中国产生了,如1980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而尤其以中期兴盛一时的先锋或前卫美术为主力军。1985年兴起的“85美术新潮”和1989年2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艺术展,使得先锋主义在美术界达到鼎盛期;而从90年代开始至今,先锋主义美术诚然仍在生存,但主要是采用了一种奇特的方式:由主流潜入边缘、从国内学界搬到国外画廊(美术市场)、从审美的形式实验演变为突破法律、道德与宗教极限的极端行为、在国外赢得名声而在国内悄然共存。
面对革命主义的极端形态——“文革文艺”,中国的先锋主义是以艺术形式为突破口的。1979年,画家吴冠中在美术界率先冒犯当时占主流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内容至上信条,提出“形式美是美术创作中关键的一环”(注: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美术》1979年第5期。)。他的形式优先的先锋美学搅动起后来一度曾蔚为大观的“抽象热”。可以说,中国的先锋派美术是以“形式”为突破口、通过“抽象热”进军方式而登场亮相的。栗宪庭在反思先锋美术思潮时主张“重新来鉴定中国前卫艺术的规则,寻找中国前卫艺术的标准”。他提出中国先锋派或前卫艺术的两条美学标准:第一是同时承担社会文化批判与语言批判的双重任务,第二是基于西方原本之上的再创造性。第一条是说艺术的反叛要服从于和服务于中国的文化变革需要,即“社会革命和思想解放”。第二条是基于第一条而产生的:“由于我们的关注点不同于西方,艺术家在使用西方现代艺术语言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异,这种变异可能会产生‘再创造性’。”(注:栗宪庭、刘淳:《回顾中国前卫艺术——栗宪庭访谈录》,《天涯》2000年第4期。)上述两条美学标准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第一条在先锋主义思潮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而相比之下,第二条的实绩则远为有限。其实,只要同现代性的其他颜面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时期先锋主义美术思潮同当时的文化主义是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还带有强烈的革命主义色彩。栗宪庭在回忆1985年发生的“美术新潮”时说:“从1985年至1989年间,我们几乎是将西方包括六十年代以后的艺术样式都尝试了一遍,各种各样的语言样式都拿进来。其意义在于中国艺术家自己为自己提供了一次对西方现代艺术全面实验的机会,在短时期里的一种演示,既然引进来了,大家都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它。因此,在今天看来,’85美术新潮是一个全面的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的文化运动。”(注:栗宪庭、刘淳:《回顾中国前卫艺术——栗宪庭访谈录》,《天涯》2000年第4期。)先锋美术自觉地承担起了那时迫切的文化批判任务,并且实际上演变成“一个全面的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的文化运动”,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当然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从20世纪革命主义传统中吸取合法性资源。
在文学领域,尽管先锋主义的发轫可以追溯到文革后期的某些诗歌与小说实验,但是它直到1985年马原、莫言和残雪崛起于文坛时起,才在激进的“先锋小说”中聚集起强大的声势、产生引人注目的重要实绩(注:有关当代先锋文学,见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随后有格非、孙甘露、苏童、余华、洪峰、北村等相继走入先锋文学的激进实验场。这股先锋文学浪潮是在由文化主义支撑的“寻根文学”正充当主流的时刻破土而出的。他们不满于“寻根文学”在语言表述和文学观念上的因循守旧,而此时又欣喜地瞥见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新潮。“自80年代中期以来走红中国文坛的‘先锋小说’,曾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感召”(注:王一川:《借西造奇——当代中国先锋小说语言的审美特征》,原载《外国美学》,第16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0页。)。具体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1982)这一事件的有力推动和感召下,马原、苏童、格非和余华等作家从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西方语言中获得了新的写作灵感,投身于一场自发的或不约而同的‘先锋’运动。以新的语言为焦点实施突破,不失为这些‘先锋’小说的鲜明特色之一。而引导他们历险的主要范本,正是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及现代主义语言”(注:王一川:《借西造奇——当代中国先锋小说语言的审美特征》,原载《外国美学》,第16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1页。)。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可以用自由的新形式去表现富于拉美地域特征的“魔幻”民俗奇观,中国作家难道就不能用解放了的汉语文体去传达新的生存体验?
汉语表达方式的激进变革,是这股先锋思潮的一个主攻方向和主要特征。作为这时段最早且富于开拓意义的先锋文本,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收获》1985年第2期)可谓汉语形式变革的始作俑者,它从多声部对话、复线交叉错时叙述、多层次与多声部叙述等方面体现了先锋主义在汉语形式或文体上的美学历险(注: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281页。)。单纯从汉语形象的变革看,这批先锋派的先锋性就集中体现在“间离语言”这种新的语言的创造上,具体说包括如下方面:错乱叙述体、“我…”式反复句、模糊性人称与叙述干预、间接引语、隐喻形象、白描传统的复活、仿拟与反讽等(注:王一川:《汉语形象美学引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160页。)。与在,80年代中期文坛盛行的“寻根小说”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相比,这里的先锋突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决不限于小说语言或文体变化。这种由语言出发的先锋历险毋宁意味着一场美学革命,导致整个小说美学观念的解放,带来读者阅读的根本性变化。从此时起,中国大陆文学的语言、文体、表意、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型,革命主义让位于先锋主义。
不过,这种先锋主义雄踞文坛霸主的格局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仅仅持续短短几载光阴(1985至1990年)后,就聪明地凭借其光环而席卷脆弱的文坛主流,并一举成功地取而代之。例如,莫言、苏童、余华被奉为90年代新的文坛主流的代言人或象征者,并且代表主流中国作家而在国际文坛取得承认。其实,这种先锋派从边缘向主流的移位及随之而来的先锋作家主流化变故,是不以作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便他主观上希望永远做先锋派。主流舞台的掌声和鲜花,绝对会在不知不觉中无情地挫伤大部分先锋作家的持续的先锋意志,而迫使他们走向主流化——把自己的新鲜的先锋历险转而应用到新的主流审美表现领域中。当他们这样做时,即便是自己想持续先锋,也不得不遭遇这样的命运:先锋一旦席卷向主流,就会遭遇来自主流河道的强大的变形(抵抗或拆解)作用,从而反过来被变形——这就是迅速失去先锋性而成为新的主流。这一点其实正是先锋主义成功的一条规律:首先以先锋姿态突破主流控制、继而自己移位为主流、最后丧失主流品格。所以,完全可以说,先锋主义一旦从边缘移位为主流,就必然会丧失原有的先锋性。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奇怪可遗憾的。
当昙花一现的80年代后期先锋派因为激变为主流而迅速趋于淡隐或归于沉寂时,姗姗来迟的刘恪就似乎成了20世纪90年代少见的坚定不移、独树一帜而愈发孤独的先锋派风景。刘恪的先锋写作主要体现为“跨体小说”创作。在他的“诗意现代主义”系列(含《孤独的鸽子》、《一往情深》等中篇)和长篇《南方雨季》里,可以见到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跨文体尝试:各篇破例按散文诗节松散地排列,显出了某种如诗如散文的跳跃“节奏”;常见的几种体裁如小说、散文、诗、日记、法律文件、地方志及引文等都挪用进来;叙述焦点不在故事之内而竟在故事外,这导致本应完整的故事被经常的叙述干预切碎,令读者坠入由许多片断缀合成的故事迷宫里;看来写了若干人物之间的复杂的恩怨纠葛,但这些都是片断的和模糊的,随处可见瓦解、纷乱或神秘等。我们面对着一种不妨叫做“跨体小说”的新东西(注:王一川:《杂语沟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五、先锋主义的没落
如今,当现代性车轮隆隆驶入21世纪时,中国还存在真正的先锋派?先锋派本来就已经迟到很久了,而今又不得不面对着西方先锋派早已成过眼云烟的残酷事实。那么,中国的先锋主义该往何处去?我想,随着现代性本身移位为反本质、反深度、无主题、无作者或无人的后现代性,向来只知标新立异、奋勇向前的先锋主义,除了落入后现代性已经摆下的陷阱中,还会有别的出路吗?后现代是现代性内部的价值允诺遭遇严重质疑和自反性精神演变到极致的产物,它既立足于现代性内部又要对现代性展开清算,既极端先锋又极端反先锋。正是在后现代怀抱中,先锋的突围最终落入反先锋陷阱。换言之,在后现代的解构浪潮中,先锋主义所赖以支撑的基本的“知识型”(episteme)已经丧失了最后的根基。正是从这种“知识型”中,先锋主义者及其信徒们曾经获得基本的话语资源。
实际上,随着既极端先锋而又极端反先锋的“后现代”思潮于199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先锋主义就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了。尽管还有少量先锋派如刘恪等残存着,但从总体上看,先锋主义的根基已经镂空了。诗人于坚的《短篇之97》这样描述中国当代“先锋派”现状:“这一代人已经风流云散/从前的先锋派斗士 如今挖空心/思地装修房间/娃娃在做一年级的作业/那些愤怒多么不堪一击 那些前/卫的姿态/是为在镜子上 获得表情/晚餐时他们会轻蔑地调侃起某个/愤世嫉俗的傻瓜/组织啊 别再猜疑他们的忠诚/别再在广场上捕风捉影/老嬉皮士如今早已后悔莫及地回/到家里/哭泣着洗热水澡 用丝瓜瓤擦背/七点钟 他们裹着割绒的浴巾/像重新发现自己的老婆那样/发现电视上的频道”这里用“装修房间”、“娃娃在做一年级的作业”、“晚餐”、“洗热水澡”、“擦背”、“浴巾”、“电视频道”等日常生活词语系列,展示了“先锋派斗士”在日常生活激流中无可奈何的没落或转变。
中篇小说《先锋》以调侃或戏谑这一独特方式,勾勒出中国先锋主义的兴衰过程,以及它向“后先锋”或“后卫”转变的轨迹(注:徐坤:《先锋》,《人民文学》1994年第6期,收入小说集《先锋》,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小说主人公撒旦是1985年著名的先锋主义流派“废墟画派”的领袖,后来在1995年又成了“后卫画派”的首领。先锋主义的兴起原因,在这里被归结为城市里“艺术家密布成灾”,也就是艺术家人口过剩:“那时侯,这座城市的大马路和小胡同里,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像灰尘一般一粒粒地飘浮着。1985年夏末的局面就是城市上空艺术家密布成灾。他们严重地妨碍了冷热空气的基本对流,使那个夏季滴水未落。干旱一直持续到了秋天。各种传染病相继流行,密云水库水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城市饮用水短缺,工业用水产生危机。郊区的农民更是叫苦不迭,他们悄悄到庙里举行各种祈雨仪式,暗暗诅咒是哪个挨千刀的作孽,得罪了龙王爷。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这竟是因为城里艺术家太多的缘故,全是让精英密集给闹的。”艺术家的过剩导致了整个城市生态平衡失调,出现全面的生存危机。而“艺术家们自己也正憋闷得喘不上气儿来”,盼望着变化。“这是一群没有行过割礼,或割过以后又顽强再生了的艺术家,循规蹈矩的现实主义日子是不情愿再过了,总在琢磨着换一个新鲜的活法儿。”
正是这样,先锋主义诞生了:“年轻的画家们在撒旦的煽情指引下,半信半疑厌厌倦倦地跟着他来到废墟。刚一进去,他们的眼睛就“刷”地被刺了一下,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废墟以那样生动的存在无情地剥落了画家们的伪装,照得他们近乎赤身裸体,立时让他们感到四肢瘫软无力。原来废墟是真实存在着的,是先他们许多年就早已存在着的。它充满着并贯穿了他们诞生与成长的这个世纪。废墟就是废墟,废墟不是他们在脸上刻意修剪出的那种参差不齐脏兮兮毛烘烘的玩艺儿。废墟成为一种象征和隐喻,昭示着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命题。废墟竟是那么一种有着无尽含义的东西。它存在着,人们却忽视了它,一直都没有去破译这个谜。”震动中国的“废墟画派”就这样出现了。它不是来自什么崇高的理由,也没有高远的抱负,而不过是在“废墟”上诞生。它的一切都似乎是无意识的或准备不足的。如此解释先锋主义的诞生,等于是化雅为俗,以俗拆雅。
先锋主义在中国会有着怎样的命运?小说的探讨值得注意。叙述人继续说:“大张旗鼓地主了一阵子义以后,一点儿惊天地泣鬼神的变化都没有发生。该吃饭还吃饭,该睡觉还睡觉,该画画还画画。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改向哪个方向。弄得撒旦他们心里反倒有些泄气,空落落的,白担惊受怕趾高气扬地企盼了一场。”按叙述人的看法,先锋主义与中国社会进程严重分离或游离,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1985年的情形基本上就是这样,什么都主义又都主不了义。什么都先锋又都先不了锋,什么都存在又都不存在,什么都错了位都变了形,什么都看得懂又都看不懂。”先锋主义,其实就等于“先锋主不了义”。先锋主义还有什么用处?小说就这样对先锋主义作了空前辛辣的讽刺与批判。
随后,各种各样的先锋主义、甚至出人意料的“后先锋”和“后前卫”都粉墨登场,直把功成名就的“废墟画派”看傻了,吓呆了,迫使他们激烈地内讧,“忽喇喇地作鸟兽散”。心灰意冷的撒旦躲到深山古寺里去画佛像,没想到被东方美妇人巧妙地以法院传票的方式又传回了尘世,加入到先锋主义的“新一轮艺术流通”与“拍卖热潮”中。这时的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了“后卫”,举办“后卫画展”。这个画展的空前成功,又掀起了一股后卫浪潮。“冲冲冲/我们是新时代的后卫/冲冲冲/我们是新时代的后先锋”。但与新的成功相伴随的,却是撒旦本人感觉“头痛欲裂,一阵猛似一阵的的神经抽痛折磨得他半死不活”。不得已中,撒旦潜入美术馆把自己的金奖作品《活着》的画框切割下来,扛着它重新去到废墟,与康熙、乾隆、武则天、李莲英和海伦等不期而遇。在迷离恍惚中,体验到更深的痛苦的撒旦,在轰隆隆的过山车上让自己化做“无数殷红的花朵”和“一地的绚烂和蓬勃”。此后,撒旦的画框被路人拎回家改造成洗衣机和电冰箱托架,还获得一笔专利发明奖。喧嚣一时的中国先锋主义和后先锋主义,就这样衰败了。
这种小说家笔法可能过于尖刻了,对中国先锋主义的肯定性价值缺少应有的积极发掘,但另一方面,毕竟从一个夸张与变形的侧面,曲折地透视出先锋主义的盛衰轨迹,呈现了它因与中国社会状况相疏离、并植根于低俗本能而必然衰败的命运曲线。这似乎正是先锋主义在中国的必然命运,它是不配有更好的命运的了。当然,先锋主义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文学变革。先锋主义诚然已经退场,但文学变革依然会不时地发生,这种变革是要适应人的生存体验的变化需要,因为文学只能唯生存体验之马首是瞻。只是,这种文学变革不会再轻易地竖立起先锋主义的大旗了。而如果你在当今大都市中心商业步行街发现竖立起来的醒目的先锋大旗,那么,你不必奇怪:它们往往不过就是这个文化消费时代层出不穷的文化商品(楼盘、盒带、汽车款型、发型、时装等)的一种必要的“商业”包装而已。近年来,越来越怪异和极端的“行为艺术”或“前卫艺术”一心以国际文化市场为主要突破目标,正是一个明证;而同理,在近年所谓“先锋戏剧”那里,“先锋”已经成了戏剧走向商业化的眩目“包装”或标签。
从上面关于先锋主义的简要回顾中,不难看出它与我国20世纪独特的文化语境及其演变状况密切相关。它的晚生早衰特性乃至它的没落,都与特定文化语境的特殊需要密切相关。它在文化启蒙的急切呼唤声中错位地应运而生,以及在文化消费主义的时尚大潮中无可奈何地淡隐,无不取决于文化语境的具体需要。当着作为现代性的主要颜面之一的先锋主义趋于没落时,现代性本身的症候就必然地暴露出来了。问题在于,这种没落意味着什么?表明现代性正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还是转向一个新的时段?我的初步判断是后者。但对此的论证需要另作专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