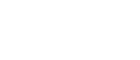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哲学叙述的问题域。对“当代中国哲学”而言,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也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关键词:文化身份 当代中国哲学 哲学的始端与视阈 哲学的演化逻辑
1.最近,“中国哲学”这个称谓是否具有“合法性”,“探寻当代中国哲学之路”或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成为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中国哲学”或“当代中国哲学”能够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表征的是处在“文化失语症” 中的我们对失语状态的摆脱欲望和文化的建构姿态。对于这个话题,人们谈论的大多集中在建立“当代中国哲学”的必要与否,文化与知识资源的储备条件与状况,在理论与逻辑中为这种建构欲望的实现提供是否合理、是否可能的说明等问题上。毋庸讳言,这些话题背后隐匿的是在“中西、古今”文化对话中所形成的文化比较心态,这种比较心态来源于以“天下”作为世界理念的大国,在失去经济、政治优势以后,力图在文化上为可预期的未来找到心理和意志上的自信。这种比较的欲望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本能。冯友兰先生曾对中国文化界热衷于文化上的中西比较的现象作过解析,他强调在“比较”中我们容易陷入康德的知性悖论(Antinomy),亦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实际上,处在这种文化比较中的我们只能在詹姆斯的“意志信仰”中寻找合理性。我们且不谈这种“比较”在知识论意义上的可能与否(这应是解释学的话题之一),这里对我们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姑且把“中国哲学”的称谓作为我们哲学性存在的不证自明的天赋前提,姑且我们是能够以哲学家的姿态构建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发问的,需另外行文论述),那么,这种哲学应该说些什么?怎么说?应该确定什么样的意义域才会使得这种哲学是合理的,并且可以称得上是属于我们的哲学?或者说,我们要构建一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的哲学?本文只是想在历史与经验的叙述中,描述一条处在当代境遇中的我们可以接纳的思路。一切空泛的口号式的呼吁,除了能引起向前行的人们的回头一望之外,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重要的是进入问题本身。
2.虽然“哲学”属于西方话语,但在近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它已经成为对我们的精神活动进行描述的文化框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存在的意义的上承认并接受了“哲学” 。在我们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是对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进行反思,并以“发问”为主要特征的精神批判活动。这是从历史中搜寻的对于哲学的具有普泛性的规定,以此来把握人类各种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意义,是有广泛可理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观察视阈。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活动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身份问题紧密相连。可以说,哲学与宗教是人类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身份问题的核心。文化身份本身的意义在于某个社会共同体在文化的创造中确定精神文化之 “我”。有了精神文化之“我”,才可能拥有文化的述说和文化的创造(作)。以哲学和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创造过程,也就是确定文化之“我”的文化身份的过程。哲学之“说”与“做”,不是在文化身份之外的“说”与“做”,因此,我们应在确定文化身份的视阈中来看待“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域。
3.一百多年来,文化的中国 在多种文化的对话中,在器物、制度、文化等不同的层面,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我们经历了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和文化的中国在“中西、古今”的境遇中,总是在寻找着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和位置。在这用生命和鲜血构成的寻找过程中,我们总是陷入不知道“我是谁”,“我应该向何处去”的困惑。所以至今我们还在寻找着我们的出路。这种寻找是在我们的精神与文化的境遇中,以“我”的存在意义为原则的历史选择。问题是一百年来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也失去了我们的文化身份。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两个视角来看。
首先,从当下文化对话的角度看,我们现在患了精神文化的“失语症”。台湾作家龙应台曾以文化的自觉发出呼唤:“全球化视野中‘我’在哪儿?” 这一问,确实道出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现状。一百年来,我们处在对话的语境中。但是,今天的我们在文化上是那样的尴尬,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作为文化存在的必要的身份,丧失了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记忆。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对话的视阈中,我们不知道精神文化中的我(我们)是谁?在我们所拥有的精神文化资源中,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抑或是外来的西方文化?人们可能会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但实际上,当下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相当大部分却是在图书馆里,研究者的桌案和学校的课堂上,或者仅具有历史回忆和旅游观光的意义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已明显弱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在可以称作“我们的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是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了;我们不是已经习惯了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问题吗?近些年来,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大举进入我国,并逐渐在精神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成为了我们当代社会的主流话语。我们不是吃着洋快餐,穿着西服,乘着洋车,住着洋房,过着圣诞节吗?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浸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在文化对话的视阈中,在失去自觉意识的对话框里,“我们”同样也失去了对话的对象。我们既不知道我们在和谁对话,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和谁对话。所以,我们才有了从存在主义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到文化热、国学热,以及马克思热、现象学热、解释学热等精神文化寻觅的轮回。在这种精神文化的轮回中,我们在寻找着对话中的我们和对话中的对象。应该说我们还处在精神文化的迷茫状态。在文化对话的视阈中,失去了文化身份与对话对象的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进行对话。在历史上,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对话方式。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体用”、“和合”等对话方式。通过不同的对话方式,生成着不同的原生文化。如近代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全盘西化都属于“体用”的对话方式。而宋明理学,既有“体用”,又有“和合”。今天的我们却在这种“体用”、“和合”等对话方式中来回游荡。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忘记了我们是谁,丢失了我们应该的对话对象;我们已经不知道应该对谁说,应该说什么,我们好像丧失了对话的能力,我们患上了文化的失语症。我们不是又开始争论什么“纲目”(体用)、“合和”,白话、文言的是与非了吗?应该说,关于“中国哲学”这个称谓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讨论,“探寻当代中国哲学之路”或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是我们在这种窘境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姿态。
其次,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忘记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使命的担纲,一直寻找着对话中的“我”的文化身份。在历史的维度中,这种意义上的“寻找”经历了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以及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各种模式的转换 。但是,这些貌似不同的“寻找”实际上都是在我们传统的体用不二的把握方式中打转转。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说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土身份的眷恋和守成愿望;而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西化”倾向,在李泽厚这里体现为“西体中用”,这种倾向代表了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惰性的无奈,以及面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双重挤压下所不得不做出的应答。实际上,这里蕴涵的是如何处理守成和开新的关系问题。这种对文化对话中的“我”的身分进行寻觅的努力,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和国学热,乃至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呼吁中 。
4.自晚清学者黄遵宪把“哲学”这个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哲学就逐步附着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成为我们的精神文化框架。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与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身份的寻找是同步的过程。与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对话主题相适应,在哲学上形成了一个寻找属于中国哲学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当以上一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胡适、冯友兰、熊十力、贺麟、金岳霖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上所做的工作为代表。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以西方哲学立场优先为特征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与扛鼎之作 ,而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贞元六书》、贺麟的《新心学》、以及现代新儒家等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则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在这些学院派哲学创作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实用理性的姿态进行了以马克思命名的哲学创作,叫做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在中国哲学的创作中应该享有独特的地位。解放以后李泽厚在哲学体系上的探索工作也应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这个寻找中国哲学的文化运动一直延续着,并传承着确定文化身份的文化使命。应该说,一百年多年中国哲学的创作史,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哲学文化框架(这种框架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释解、改造中国本土文化,构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场景需要的“新”哲学的过程。不管这些哲学是否能成为公认的体系,这种创作中国哲学的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到当代寻找中国文化身份历史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如此看来,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场景不是孤立的哲学想象,而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寻找中国文化身份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当我们面对“当代中国哲学”“应该说些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域时,恐不能离开如上所述的中国哲学问题的历史背景和言说语境。我以为,中国文化身份问题是探讨“当代中国哲学”“说什么”的历史与逻辑的起点。这个起点规定着“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域限。
5.“哲学”在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历史传承中有着不同的演化逻辑。对这种演化逻辑的梳理有助于对“当代中国哲学”问题域的确定。
在西方哲学中,对哲学问题的探究始终存在着一个我们从哪儿开始思考,从哪儿开始发问,从哪儿开始说起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的始端问题。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中,各种不同形态的哲学实际上都设置了某种始端。在西语语法结构中,在形式性的思维习惯下,确定了哲学从哪儿说起的始端,也就预示着确定了在这个始端中所合逻辑地规定着的某种观察与解释视阈,也就是确定了它的问题域。无论是以逻辑的同一性为基础的本质主义(或者称之为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还是尊崇非理性直觉的怀疑主义、神秘主义抑或宗教神学,都离不开对始端的设计。这种设计在哲学上也叫做终极预设。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种解释和把握世界的方式,那么,终极预设在确定哲学的始端、观察和解释视阈中,就成为了哲学解释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根据。实际上,在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自我觉知与把握的历史中,每一次哲学问题域的转换都意味着哲学始端和视阈的变更。各种不同形态的哲学都是通过设置不同的始端与视阈,去应对人类精神的发问。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哲学问题域演变的历史。哲学问题域的演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哲学发问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哲学思考和叙述的始端及其与之相应的观察与解释视阈的转换。如果说哲学的发展体现为哲学问题的演变,具体为哲学发问方式的改变,和哲学思考和叙述的始端及观察、解释视阈的转换,那么,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中,从大的范围讲,应该说有三种哲学的始端和解释视阈,即:古代的本体论;近代的意识(认识)论;现代的体现在语言论中的对“可说”的消解,并走向“沉默”和“无”,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语言论。从具体哲学形态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休谟与康德、黑格尔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等,都存在一个哲学发问方式与叙述方式的转变,由此引起哲学问题发生变化,导致哲学的始端及观察、解释视阈的转换,从而形成不同的哲学体系和形态。可以看出,西方各个不同哲学形态的演化,在哲学问题、思想的起点(始端)、思考方式、观察和解释视阈等方面都是断裂的,也就是说在哲学意义域上大都是重新构造。所以,西方哲学呈现为不同的哲学问题域、始端、观察和解释视阈的前后相继为特征的演化逻辑。
与西方哲学的这种演化逻辑不同,中国哲学的历史则呈现为各个不同时期的哲学之前后相继,在于对于经典进行的考据与注释活动所形成的意义上的差异,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那些经典文献。孔子的“述而不作”对中国学术的传承影响至深。从中国的学术史看,先秦的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明末清初的朴学等,其学术传承和沿革在学术的根本处仍只限于对中华元典的考据、注疏、义理的阐发。虽然在学术史上有考据注疏与义理之分,在学术方法上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别,但在根本处还是离不开经典的问题话语和语境。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中国学术的史官文化和“师承”、“道统”特征,自子学时代孔子删定六经始,《诗》《书》《礼》《易》《乐》《春秋》遂成为经典。汉代把五经立为官学,独尊儒术,始有经学,并分立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经学的“师承”与“道统“中,由汉朝的“五经”,南朝的“七经”,唐朝的“九经”,到宋朝的“十三经”,一切学术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些“经”来进行的。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视这些“经”为神圣与崇高。中国学术的实质不是要对那些远古的礼治、根据进行批判性的发问,而是在以元典为圣的前提下,只能微言大义。所以,在中国学术历史中只能呈现为“经”的多少的量的变化或各个经典的位次的变化。所以,中国的学术是注经而立说。“师承”与“道统”、经注与释义是中国学术的主要特点。这种学术演化的特点在道学和佛学的传承中也有着相当的体现。作为中国学术之精粹的哲学更是如此。如果将儒释道看作中国哲学的文化资源,那么,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与思想传承都是在以儒释道为载体的文化演化中体现的。这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没有西方那种哲学问题的变更,也没有由于哲学问题的变更所导致的哲学发问方式和观察、解释视阈的断裂而形成的哲学形态的演化。朱熹在注解周敦颐的无极太极学说和二程的体用一源思想时,指出了中国文化语境的哲学理解与传承特征:“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不然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之所传也。”据此,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哲学的演化逻辑:⑴由圣人、先贤依天、地、人三才之万物之理,确定哲学作为“内圣外王”之道的经典。如伏羲、周公、文王演八卦之《易经》,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等。这些经典确定了中国哲学的大学之道。⑵后学只能是在这些经典所述之大学之道中进行微言大义之演绎。此演绎也只是“述而不作”之“述”。所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鲜有离经叛道、另起炉灶的依问题意识原则来构建的新的哲学解释体系。⑶ 中国哲学的演化逻辑原则是既要“述而不作”,又要“返本开新”。“作”只能为先贤、圣人所为,后学只能在先贤之“作”中寻找“述”的路径。而“述”的主旨与使命则为“返本”与“开新”。所以,中国学术或中国哲学的主题即为:何谓“本”?何谓“新”?如何“返本”?如何“开新”?而其“开新”的根本在于如何“返本”,返什么样的“本”。也就是如何确定“本”与“新”的标准。
如果说中、西两种不同的哲学思考方式和演化逻辑及其原则,在哲学与文化的历史中已被哲学或文化的担当者所接受,那么,其就应作为“当代中国哲学”不可逃避,并且必须面对的文化和哲学的学术资源,也应成为“当代中国哲学”话题的构成要素,或作为其问题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6.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文化身份的寻找过程的艰难,以一种历史比较的眼光去梳理中、西学术乃至哲学的演化逻辑,实际上在我们叙述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思考前提设定,即:任何哲学的基本面貌与言说话题,都离不开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其说什么,怎么说,都只能在其所面对的文化资源中寻找答案。哲学话题本身的纯粹性背后的意义与历史和逻辑不可分割。历史的意义在于为我们“说什么”确定语境,逻辑的力量又使我们“怎么说”有了
不可逾越的选择可能。这种思考方法的潜台词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发展来解释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发展的经济决定论的思考模式不失为一种解释模式,但哲学、宗教只是依据自身的演化逻辑去回应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因此,对哲学本身的面貌起着直接作用的还是哲学的话题和语境的历史演化,以及在这个历史中蕴藏的演化规则。我们是依这样的前提认识来观察“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也就是说,面对“当代中国哲学”的话题,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们以“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德国哲学”“法国哲学”,抑或是“东方哲学”、“西方哲学”等名称去称谓某种哲学,这里的“哲学”一词并不是纯粹意义的,而是在表明某种文化身份的意义上使用的。这些能够作为文化身份的哲学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存在,其存在的理由在于哲学的问题域和与其他哲学能够相区别的独特的传承方式和演化逻辑。我们恐不能将“黑格尔哲学”或“海德格尔的哲学”就当作“德国古典哲学”或“当代德国哲学”。因为这种具有民族性文化身份意义的哲学形态,不是某个哲学体系或某位哲学家的思想所能完全体现得了的。所以,对“当代中国哲学”而言,并不是要去确定某种哲学解释系统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唯一性,而是要依据哲学的思维逻辑“去说”、“去做”。
7.依据上述所述内容,我认为应该在中国文化身份问题中,并且依中、西学术或哲学的演化逻辑去思考、确定“当代中国哲学”“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亦即确定“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域(或意义域)。实际上,这个意义域并不是我们的主观设定和想象,而是一定历史范围内人类某个共同体对于自身存在的感受和反省方式。因为“哲学不是一种现成的‘学问’,而是一种对人的现实生存和社会生活的深层根据进行不断追问和审视,并在这种追问中不断生成自身的‘活动’” 。因此,我们只能依历史的述说,为“当代中国哲学”“说什么”,“怎么说”、“做什么”、“怎么做”提供可能的原则和思路。
第一,“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主题。正如福柯所说:“也许最确定无疑的哲学问题是此时此刻的问题,亦即在这个非常时刻我们是谁的问题” 。无论是从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来看,抑或是从中国近代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哲学自从成为中国的本土话语,便与中国的历史命运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的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其主旨应是为作为中国之“我是谁”寻找一个合乎现代理性的文化坐标,这个坐标应是中国文化身份的精神内核。这样,“当代中国哲学”就必须是对近代中国文化身份寻找运动的“接着讲”。这种“接着讲”是在“对话”中进行的,因为“对话”是我们不可逃避的精神文化境遇。我们必须面对的精神文化背景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对话,还有已经融入我们政治、精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话题域。
第二,就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讲,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哲学之述”与“哲学之作”的历史与经验。我们在“对话”中的“哲学之述”与“哲学之作”,已经不会再是那种“述而不作”或“只作不述”了,而应在“述”与“作”中导入中华民族的融通智慧。所以,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叙述方法上,既要汲取科学理性的问题意识,在哲学之“追问”中依人类的思维逻辑去构造合乎理性的解释系统,又要在“形而上“的“根源意识”中寻找人类所拥有的终极情感。前者可能形成独特的科学观、政治与社会观,后者可能为我们的宗教情感找到合适的去处。这样,“当代中国哲学”的“说”和“做”可能就会有了文化身份的独特意味。
第三,哲学以及宗教等作为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精神和意识形式,都离不开表现为始端和视阈的终极预设。无论是从肯定的意义上去积极地设置,还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去消极地怀疑,都有一个所从出的起点或依据,即使是怀疑、发问也得有个“疑”和“问”的所以然。因为“疑”和“问”作为一种行为内含的是“意欲”,这种“意欲”源于作为人的“我”(不管是“大我”还是“小我”)的存在性。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哲学的构造原则。对“当代中国哲学”而言,其始端(哲学从哪儿说起)和视阈(哲学能说或做什么)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哲学的始端和视阈作为一种终极预设,是处在无限的预设循环中。也就是说,任何哲学都要去设置一个始端,这个始端从功能上确定着其哲学说明和解释的阈限,并且只对其所源出的语境有意义。所以,终极预设也好,始端也好,都是要变更的,即使是上帝也要不时地变换着身份。我们的哲学也不会例外。
第四,“当代中国哲学”以“认定”的方式确定的终极预设,是否有意义,或者说是否有存续的价值,取决于历史语境的认可和历史中的人类某种共同体的接受与否。这里,时间和历史是我们对“当代中国哲学”进行评价的坐标。
不论“当代中国哲学”是否可能,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如上的原则恐是难以逾越的。如果从本土文化的情感出发,我们盼望在中国的哲学平台上,能够出现可以称作“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潮流和真正意义的“中国哲学家”。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
2.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冯 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学术月刊》2004年第3期。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
6.《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
7.《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8.贺来:《“在批判旧世界观中发现新世界”与哲学的当代合法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
9.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Seek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bstract:I think, as a meaningful subject,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is not a pure academic creation but an issue threshold that should determine its philosophical narration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 As for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n the one hand it can’t part from the historical destiny of Chinese’s seek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since the mordern times,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to find its narrative ways and philosophical languages in the evolutional logic,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t is in the history that “the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determines its narrative beginning and visual threshold. It is in the historical reception that “the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seeks the grounds for its survival significance. The philosophical form is needed in China in the contemporary times, which belongs to itself and suits its cultural identity. What is more, the philosophers are needed, who belongs to China itself.
Key words: the cultural identity;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the beginning and visual threshold of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evolutional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