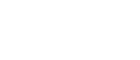澳大利亚已故著名诗人朱迪思?赖特(Judith Wright)曾大加赞赏20世纪60年代以来土著作家的崛起,认为他们敢于表征自我、发出不同于白人的声音。她在《土著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Aboriginals)[1]和《诗歌》(The Poetry)[2]两篇文章中充分肯定了凯思?沃克(Kath Walker)、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凯文?吉尔伯特(Kevin Gilbert)、科林?约翰逊(Colin Johnson)等土著作家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们在争取平等权利、抗拒白人同化等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其中,吉尔伯特的《摘樱桃工》(The Cherry Pickers,1968)、戴维斯的《梦想家》(The Dreamers,1982)、《没有糖》(No Sugar,1985)都是戏剧方面的力作。由吉米?迟创作的音乐剧《崭新的日子》同样不可小觑。该剧于1990年一经表演,即刻引起轰动,吸引了高达20万的观众(澳大利亚总人口只有2千万左右),在澳大利亚戏剧和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根据1990年舞台剧版本改编、由雷切尔?珀金斯(Rachel Perkins)导演的电影版本《崭新的日子》[3]同样大获成功。该片富有喜剧元素,充满无限活力和强烈的土著色彩。它在给观众带来欢声笑语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澳大利亚种族关系的深刻思考。
电影的男主人公是16岁的土著男孩威利,他被送往西澳首府珀斯的寄宿学校接受白人教育和基督教文化。他的土著母亲特里萨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牧师,以期赢得所有人的尊重。电影一开始,威利显得幼稚、害羞、勤奋、听话,却不清楚自己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寄宿学校的残忍粗暴最终让他奋起反抗,促使他踏上了回家的征程。他感到城市生活并不适合他,而距珀斯北部2 200公里的布鲁姆才是他真正的家,真正的天堂所在。回家的征途也是威利自身成长的过程,他变得勇敢、独立,并且辨明了自己的身份。
一
土著在澳洲大陆已经生存了5万余年,靠捕鱼、采集为生,与大自然保持着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土著在精神上更是与土地息息相存。其起源的传说“梦幻时代”创造了土著的宗教和文化,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大山,岩石,直到小石子都在梦幻时代里和精神作用联系起来。然而,白人入侵澳洲之后,他们把部分土著狩猎的土地变成巨大饲养牲畜的牧场,他们引进的国外动物再次毁掉了土著的部分食物源。土著背井离乡,被迫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虽然1992年Mabo案例成功之后,澳洲第一次不再被看做无主之地,但土著的土地权一直悬而未决。城市中与土地失去联系的土著缺乏生存能力,又没有了精神寄托,过着悲惨的生活。白人在指责土著人终日酗酒、偷盗滋事的时候,却忘了反思正是自己的入侵导致了他们目前的局面。
《崭新的日子》通过蝌蚪叔叔看似轻松的叙述,向观众展示了处于城市边缘人状况的土著的窘境。虽然圣经反复教导土著偷窃是一种罪孽,然而影片中至少有两处土著偷窃行为。一直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威利有些不安,但蝌蚪叔叔的话一语中的。他说:“我们土著要么偷窃,要么饿死!”失地土著不仅失去了食物来源,更重要的是割断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威利逃离寄宿学校的当晚,初次遇见蝌蚪叔叔等几位正在喝酒唱歌的土著。他们的歌声凄厉、哀婉:“我离家很远很远……我怀念你双手的抚摸,然而这种忧伤毫无用处,只得自我娱乐、独自面对,今晚我在等待、观赏夜景,我只想着回家。”
回家的路上,威利一行被警察关进监狱,影片借助他那晚所做的一个梦批判了白人对土著的屠杀与迫害,表达了对失去土地、饱受虐待的土著的同情。雷切尔?珀金斯谈及了这个片段的创作背景,指出她试图用舞蹈的形式赋予一幅土著碑刻以活力。碑刻上面是八位因杀死白人牛群、脖子被枷锁锁住的金伯利土著。影片中,舞蹈的背景音乐是“听新闻吧”。吉米?迟指出这首歌的创作与1980年的Noonkanbah采矿抗议事件密切相关。那时,白人开采公司开来大量卡车,运送开采设备,挖掘土著的圣地。土著因抗议白人开采而被关押、暴打。电影中,威利梦到那些上着枷锁的土著长辈在丛林中一边跳着土著特有的图腾舞蹈,一边吟唱着这首“听新闻吧”:“带着枪支的白人杀戮了我们的儿子、女儿和母亲的孩子……听新闻吧,谈论着我们土著人民的忧伤,期待太阳照射四方的那天,因为我相信崭新的一天即将到来……”这首歌唱出了土著民族的辛酸史,抒发了心中的怨愤,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鼓动性。同时,它激励威利振作精神,努力生存下去,因为“崭新的一天即将到来”!威利的形象不断变得高大,慢慢升腾,他对自己的身份和未来也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和认识!
二
历史上,在大多数白人的眼中,土著一直属于次人类。“天定命运”和高科技都被白人用来证明自己的民族优越性。在白人看来,土著落后、肮脏、无知、叛逆;他们若不皈依基督教,便不能称为真正的人类。赖特在《澳大利亚诗歌中的土著》(Aboriginals in Australian Poetry)[4]一文中提出,白人对待土著的态度变化在澳诗中得到反映。赖特在梳理时发现,第一首涉及土著题材的诗歌是查尔斯?汤普森(Charles Tompson)的《黑城》(Black Town)。汤普森的土著观在当时司空见惯,即认为土著是桀骜不驯、混沌不开的次人类,因而哀其异教命运、叹其不开化状态。查尔斯?哈珀(Charles Harpur)的诗歌《四坟墓之溪流》(The Creek of the Four Graves)则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白人对土著反抗所持的常见态度。土著被称作恶魔,野蛮、可怕、懒惰、邪恶,同情用在这些非人类身上简直就是浪费。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诗人鲜有提及土著。土著越来越被忽视,变成了隐形人,即使有描写,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也还是认为土著是堕落、无望的种族。虽然情况在1938年兴起的津敌沃罗巴克运动之后有所好转,但传统的有关土著的滞定形象仍然深深地植根于白人心理之中。可喜的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涌现的土著作家致力于强调本民族生活方式的价值,增强了土著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自尊感。 影片中,白人教父总以文化优越者自居,对土著的鄙视显而易见。他要求威利努力学习《圣经》,然后去帮助在荒野中号叫的土著同胞;当威利对自己是否适合成为一名牧师感到困惑时,他的回答是“你不会希望像在布鲁姆的无用的黑鬼那般虚度一生吧?”;当威利承认自己偷窃食物时,他讥讽着说“我应该知道你体内的土著血液一文不值!”彼得?毕比(Peter Bibby)在评论影片时指出,“白人入侵以来,政府通过武力、宗教、哄骗和立法等方式将土著孩子从他们的家庭带走、将母亲与其孩子强行分离、迫使父亲远离自己的角色。这是同化。如果同化政策成功了,那么一种文化将消亡,一种独特的身份将泯灭”[5]。
1901年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就一直在鼓吹宣扬“白澳政策”。为了实现种族、文化同质的“理想”社会,白人对土著制定和实施过不少政策:屠杀、隔离、同化等。早期拓荒过程中白人为了霸占土著的土地,对土著主要采取了屠杀和驱赶的政策。1901年开始,政府意识到要保护土著,手段是将土著驱赶至政府指定的保留地,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保留地,土著完全受制于保护者:被禁止讲本部落的语言和保留本部落文化传统、不能离开保留地,没有批准不能结婚、没有公民权等。在人类学家A?P?埃尔金(APElkin)等人的倡导下,1939年联邦政府正式宣布实行同化政策。[6]同化政策的思想根基是民族主义――建立种族单一的民族,实质是强迫土著人遵从澳大利亚白人的生活方式,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泯灭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
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白人文化的虚伪,并宣告同化政策不可能完全成功。特里萨似乎是同化政策的产物,每次饭前她都要进行祷告,并期望儿子能成为牧师。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威利,他学习圣经时,在家乡与其他土著一起在海边用矛打鱼的场景时常浮现在他眼前。他对抗教父的直接导火索正是教父对土著的污蔑。威利不以土著身份为耻,反以为荣。威利反抗教父的片段以及片尾,众人反复吟唱的一首歌的歌词如下:“没有比土著的身份更让我觉得自豪的事了,看着你们强占了我们宝贵的土地,没有比看到你们用存在主义的虚假给我们每个男孩女孩洗脑更可笑的事了,或许你们现在认为我们调皮,但我会很乐意重造你们流放犯的船只,将你们运回。”片尾部分,当沃尔夫冈得知自己是特里萨和神父的儿子时,他兴奋地说:“那我也是土著人!”他的女友安妮也“记得自己被人从一群哭泣的黑色的脸庞那儿拖曳出来,送到城里以白人的方式被抚养长大。我也是你们中的一员,我也是土著人!”之后,大家一起唱着“今天每个人都是土著!”虽然结尾带有些许喜剧色彩,但用意颇深。身为土著,无需感到羞耻,而是感到骄傲;土著的民族尊严得到了捍卫。
三、结 语
《崭新的日子》呐喊出了土著的心声,唱出了土著的辛酸历史,抨击了白人对土著的迫害,重塑了土著的民族身份认同感和民族文化自豪感。影片题材严肃,却不乏幽默,振奋了土著的人心,也让观众为正在迈向“崭新的日子”的土著感到骄傲!